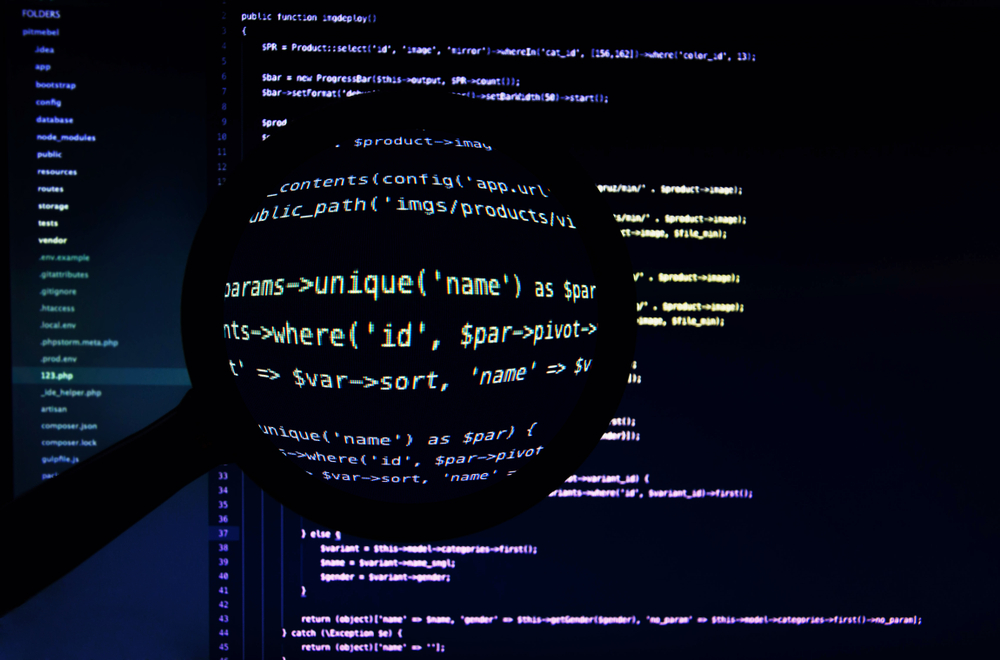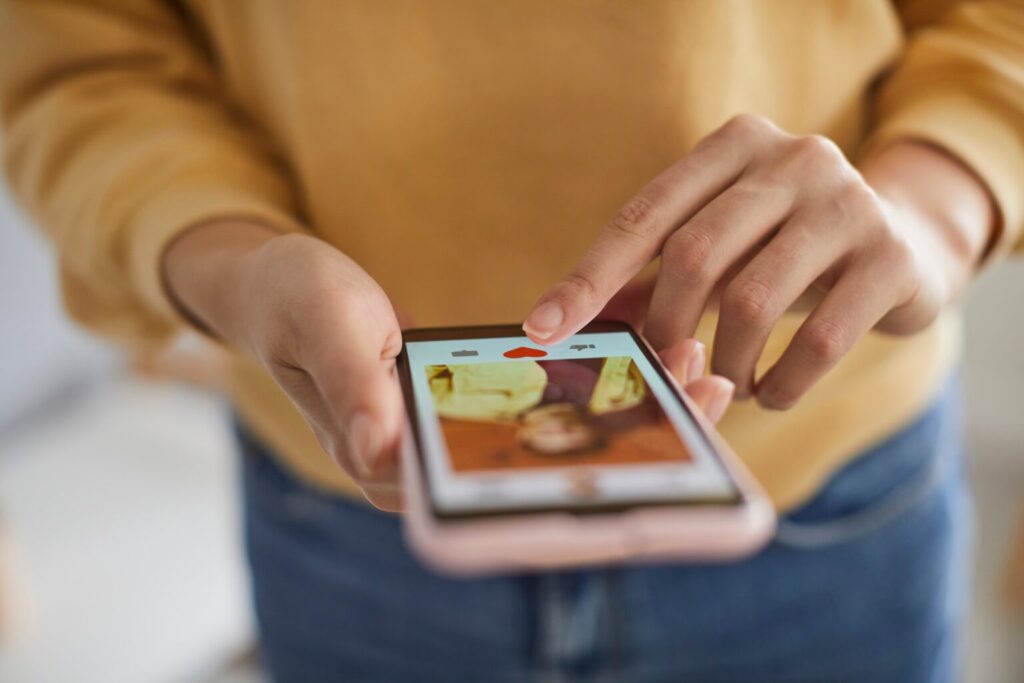深度报道精选:疫情下,无法绽放的义乌仿真花
新冠疫情以来,在义乌的航宾仿真花产业园区,40多家仿真花厂正在挣扎求存。有厂房老板为了节省成本,亲自担当送货的货车司机。有为仿真花染色的女工,在没有订单、没活可干的空闲,照样做花当作存货。在工厂一侧的空地上,堆放着几十袋仿真花半成品,何时能卖得出去,谁也不知道。
也有中国商人嗅到了疫情带来的商机,看准东南亚电子商务在最近几年的快速增长,毅然“出海”淘金,一方面摆脱中国国内制造行业恶性竞争的“卷”,另一方面赚取在国内无法赚到的高利润。“出海”淘金之路诱人,却并非坦途,“出海”商人到底要面临哪些的棘手问题?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10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义乌仿真花工厂静悄悄
出品:极昼工作室

射骨制作一朵百合花4分钱,每天张晓佳要求自己尽量做到4000朵以上。图:吕萌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许多工厂近年以来都面临物流涨价、资金链紧张等诸多压力。在航宾仿真花产业园区,40多家仿真花厂正在挣扎求存。
邓怀玉的厂房有600平米,30多个仿真花制作台已经停止运作。由于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二,原来的40位员工裁剩9位。7名女工零散地坐在操作机前,脸上映着淡蓝的灯光,专注地把百合花瓣放在射骨机(让花的梗脉成型加工注塑的机器)的模具里。不到三秒,一朵仿真百合花就初步成型。
在工厂一侧的空地上,堆放着几十袋这样的百合花半成品,颜色各异。这里积压的存货价值60多万人民币,何时能卖得出去,在邓怀玉的心里是个未知数。
邓怀玉在2009年来到义乌,开了这家规模不大的工厂。以前赶工、加班是常态,疫情却改变了一切,原本95%依赖出口的工厂流失了许多国外老客户,2020年几乎没有接到订单。邓怀玉盘算过,除去成本,每个月营业额达不到30万元就是亏本生意,现实是当前每月营业额只有十几万元。
在博艺仿真花厂,工人来自中国各地,四川、湖南、贵州、广西居多。张秀竹和张晓佳是一对湖南苗族姐妹,姐姐张秀竹断断续续在义乌打工18年了,是厂里做花手速最快的女工,一天能做5000多朵,一个月能赚起码5000元。疫情以来,她的工资平均减少了三分之一。

园区里桂花开得正盛,夜幕下,陈兰兰摘了几枝放在宿舍中。图:吕萌
妹妹张晓佳从16、17岁就跑各地打工,来到义乌做仿真花才算稳定下来。去年由于厂子效益不佳,她选择回家带孩子,今年又因为生活费紧张而回来,却发现厂子的效益比去年更差。做花的布料就堆在她身后,一天比一天少,老板也没有买新的布料回来:“已经快没有活儿干了。”
陈兰兰最近也在做花,负责染色,是仿真花厂里工资相对较高的岗位,每月有固定收入。上到小学五年级的她,通过自学而认识每一种颜色的英文编号,能把26个英文字母倒背如流。
陈兰兰到义乌已经3年了,2020年一段时间还有些忙碌,甚至老板也在帮忙染色,当时大家都以为生意会有起色。从去年开始,订单却又明显变少。时常会空闲一两天,她就和工友一起做仿真花当存货。
今年春天,她照常染好了淡粉色、浅黄色等“春色”花朵,花朵到现在还堆积在库房里。这个秋天,她又染起了深红色、橘黄色等“秋色”花朵。这些仿真花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谁也不知道。
电商人“下南洋”
出品:腾讯新闻《棱镜》

Behost在菲律宾的直播间。图:棱镜
受惠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主流电商平台的兴起,以至新冠疫情下大爆发的线上流量,东南亚在过去几年成为了全球电子商务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一些敏锐的中国商人早就嗅到了商机,利用中国国内供应链完善的优势,以及自身电商运营的丰富经验,将中国商品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卖到东南亚,以此获得远高于在国内销售所能赚得的利润。
柯培洪是福建金丝通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由于所在的泉州市的母婴产业链完善,他选择了母婴赛道“出海”。
据他介绍,目前中国工厂的制造能力强劲,导致母婴行业实在太“卷”。以纸尿裤为例,大部分中小工作坊一开机就生产几万片、甚至几百万片,而且有大量新入局的工厂和品牌,以至于市场的价格体系没法维持很长时间。“一包纸尿裤,你今天卖30块钱,明天市场上就有人卖28块,后天就到了25块。”
柯培洪透露,在中国国内的激烈竞争之下,一包40片的纸尿裤,工厂最多只能赚几毛钱,贸易商最多只能赚一、两块钱,利润率也就一两个百分点。同样的产品,“出海”到东南亚却至少能赚五到十个百分点。由于“出海”尚有一定门槛,可以遏制住大部分行业恶性竞争,让柯培洪一类商人没有选择国内的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
“出海”淘金之路诱人,却并非坦途。首先,东南亚的线上支付并不普及,因此消费者的支付方式更加倾向于货到付款。在头豹研究院看来,先买后付这种传统的支付方式,会拖慢物流效率和增加物流成本。在这种模式的市场上,平均签收率大概只有七成,剩余的快递需要销毁或者退换。
在仓储物流方面,有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企业表示包裹破损率及丢失率高是目前面临的首要难题。同时,清关障碍大、不确定因素多、物流投递信息滞后等,也是“出海”商人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富士康返乡者的归途
出品:冰点周刊

卡车司机王桂政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拉上四位返乡者。图:受访者提供
10月30日,23岁的富士康打工者高旗和妻子,联同其他工友一起选择了返乡。
离开之前,高旗在位于航空港区张庄镇的出租屋里经历了为期七天的居家隔离。刚刚解除居家隔离,高旗就从房东那里得到“(富士康)郑州园区约两万人确诊”、“最低要封两个月”等流言消息。房东劝他走,他的领导也劝他走。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像一些人那样,顺着高速公路徒步返乡。
高旗一行十余人,决定按手机上“驾车模式”导航,沿着京广澳高速一路向南,再转向商登高速一路向西,前往目的地老家登封。“导航显示驾车40分钟就到了,但是我们走路的话,不知道要多久。”高旗说。就这样,他们贴着高速护栏,在应急车道上,朝家的方向一步一步走着。
同一天,山东卡车司机王桂政一驶上京广澳高速公路,就看到四位大姐在高速上走。“高速上可以走人?”开卡车四年,他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一时没弄明白,打电话询问朋友,才知道这是一群离开郑州富士康的人,打算徒步回家。
王桂政招呼了四位大姐上车,把她们分别送到临颍县和许昌市的集中隔离点。一路上,越来越多的徒步返乡队伍出现在他的视野。他决定再回一趟航空港区继续拉人,最终这一天拉了三趟。他注意到,一路上有不少卡车靠高速公路边上停车,招呼返乡者上车,车牌来自各地:“我们开大车的这帮人太有血性了。”

梁小素在购物中心前的路边摆放的免费物资。图:受访者提供
李家村的购物中心老板娘梁小素告诉记者,过去四天她眼睁睁看着那些年轻人从20多公里外的富士康徒步经过,有的家就在附近乡镇上,有的只是路过,目的地是许昌、鄢陵。那些返乡者也都戴着口罩,不多停留、不多说话、不多添麻烦。
梁小素三年前从富士康离职,跟丈夫在李家村开了这家购物中心。过去的几天,她没算过从购物中心搬了多少物资免费发放,还有一些附近工厂的老板前来购买牛奶、方便面、纸巾、面包等,送去不远处的国道上,那里有更多返乡者经过。
白天,高旗一行人一直没有搭顺风车的念头。走到夜晚,大家体力越来越差,速度越来越慢,本来还在咬牙坚持,但夜里在高速上徒步的风险确实太大,他们才开始拦车。“今天我才知道,步行走10公里很不容易。”
晚上九点多,一辆小货车在高旗一行人招手后停了下来。那是一辆往登封送中药的车,在他们看来却像一根救命稻草。高旗跟妻子到登封后住进了隔离点,隔离点的早餐里有木耳炒黄瓜、玉米、小米粥、炒笋瓜,还有鸡蛋,午餐里有红烧肉、青菜和豆腐。他们在免费隔离点安心地睡了一觉。
80岁教师鸣冤56年含恨离世:我就是不服,我没有强奸
出品:凤凰网 – 在人间 living

汪康夫和妻子周三英合影。图: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10月24日,老人汪康夫去世。在他80年的人生中,有50年都活在“牢门”里。前10年,他是一个满城风雨的“强奸犯”,被控利用教师身份强奸两名少女学生、猥亵十名少女学生,被送往鄱阳湖城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1975年出狱之后,汪康夫为了知道当年真相,犹豫再三之下试着写信给案中的所谓“受害人”尹福珍、洪仔妹、刘淑芬等,问她们为什么检举。他又写信给当年曾经约谈这些女学生的同事贺恩莲和曹静安,以及其他同事如李品行、尹天池、贺仰豪、郭志彪等。
一人回信:“究竟为何事使您改造10年,倘若为强奸了我而受刑,这是实在的冤枉,冤枉,大冤枉,我可到法院去作证。”另一人回复:“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会到我的头上来,我也要设法把这事弄清楚。”
汪康夫觉得诧异和错愕,这到底是怎样的案件?“十年牢狱,被害人竟然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这个罪让我怎么认?”
于是在后40年,他又走进一个透明的“牢门”,低着头不断地写申诉信。尽管认定是法律程序不公毁了自己的一生,汪康夫依然相信法律程序本身。他说,再绝望时自己也不曾闹访,要维持一个读书人的体面。
他能看见“牢门”外一直支持他的妻儿,为他奔走呼吁的老朋友、律师和记者,在电视上痛哭流涕承认当年说谎的“被强奸”女学生,以及对当年发生的一切躲躲闪闪的人们……
《凤凰网 – 在人间 living》的这篇深度报道在2020年首次发表,不仅描述了汪康夫多年以来曲折的鸣冤经历,还详述了俨如罗生门的这宗所谓“强奸案”的各个版本,也谈到1966年支撑一审判决书的区区三份材料。
另外,报道介绍了汪康夫的家庭背景、早年经历,包括汪父因何背负“伪官吏”、“反革命”的铁标签,而这些标签如何让少年汪康夫抬不起头来,以至在他刚当上小学教师的那些年,“四清运动”怎样影响了他的前途。
走出梨泰院
出品:剥洋葱 people

10月30日凌晨,在韩国首尔市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救护人员在现场工作。图:新华社
被压倒的时候,徐青(化名)和朋友还挽着手,没多久就有人挤到她们中间,把他俩隔开了。朋友在中间的位置,当场就晕倒了,徐青则靠右边的墙,也比较壮,状况没有朋友那么恶劣。在徐青旁边,一个女生一下就倒在地上,很快就窒息了;徐青后面的男生更加开始吐血,血就吐在她的旁边。徐青害怕死了,手指头都动不了,硬是挺着才能呼吸。
徐青被压在人群的最前面,后面一个人接一个人,感觉有两三百人压在她身上,被压得腿已经没有知觉。警察来得慢,来了之后想从前面把压在下面的人抱出去,却一个人也没拔出去。事故发生时大约晚上10点10分,直到11点多,徐青后面的人才一点一点撤出去,最终她和朋友也获救。
“一个鲜活的生命,前一秒还在喊救命,下一秒就没有了呼吸。我当时就想着活,只想着活。(…)我真的不是矫情,当你身边接连死去三个人,你还跟他们身体贴身体,脸贴脸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绝望了。现在就想说,我活下来了,就是想说我活下来了。”
梨泰院是首尔最早的观光特区,有大量外国人居住,被称为韩国的“万国城”,也是韩国年轻人庆祝万圣节的热门地点。今年的万圣节活动,是韩国解除新冠疫情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后的首次活动。
据韩国官方通报,10月29日首尔市梨泰院地区的踩踏事故,导致至少154人死亡,另有超过100人不同程度受伤。
剥洋葱 people 采访了三位华人,他们当日从不同的地方出发,不同的时刻抵达,以不同的速度穿越了拥堵的街区,有的人提前离开,有的人一度被压在人群之下。
如果爱你不是一万年
出品:正面连接

图:陈禹
有关“分离”的困惑,驱使记者找到崔庆龙,在半年里进行了两次对话。作为一名理论和临床经验都很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崔庆龙于过去两年持续在微博上分享心理学知识。记者曾按关键词搜索,收藏了几乎所有他关于“失恋”、“分离”、“哀悼”的微博内容。
记者提到,这篇对话并非对时代情绪的回应,无关内卷、倦怠、怀旧、躺平,或这个时代的爱欲之死,但却可以对“我们为什么放不下一个人”做出一些解答。
和“依恋”一样,“分离”是人类私人经验里难以忽视的永恒话题,如同《爱的艺术》里弗洛姆(Erich Fromm)形容的那样:“再也找不到一种行为或一种行动,像爱情那样以巨大的希望开始,又以如此高比例的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