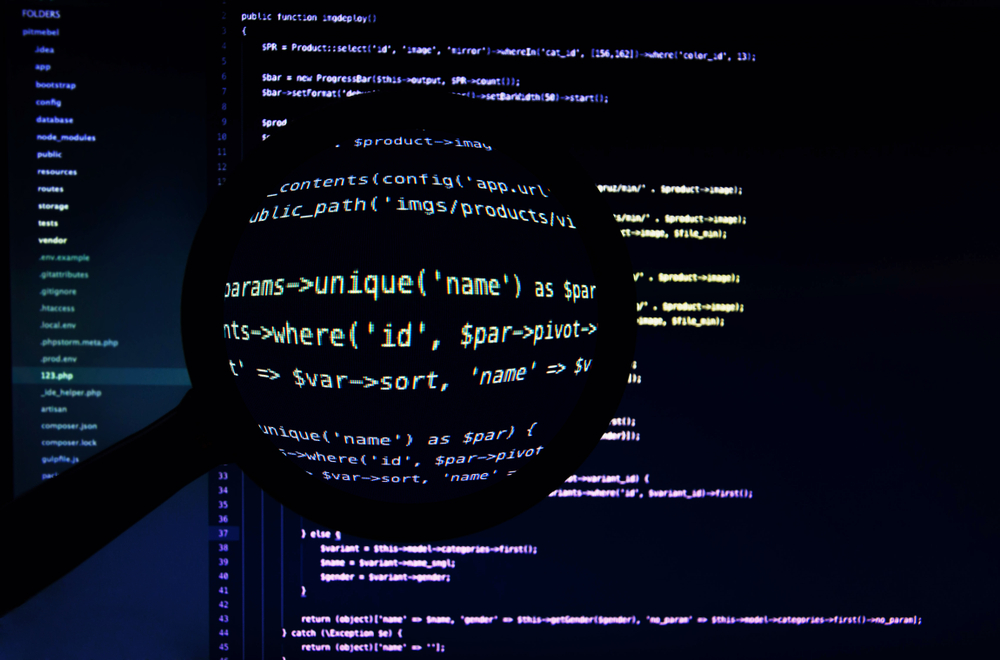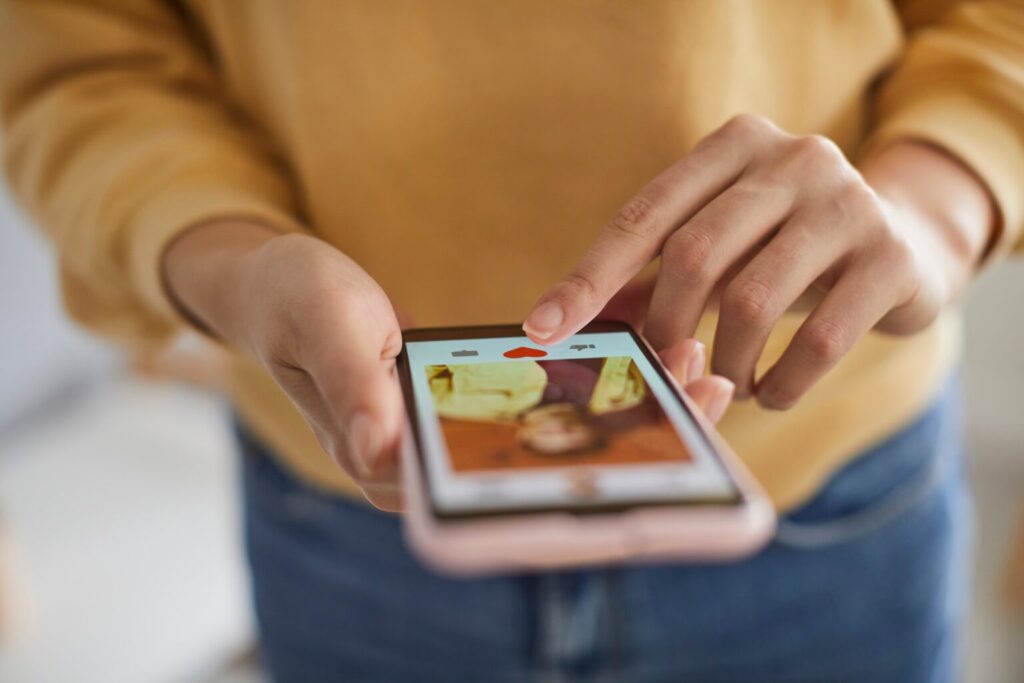深度报道精选:城里的人想出去
“北京不缺我一个打工人,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与县城也格格不入。”金融专业硕士毕业生青柠(化名)离开北京,回到山西老家县城某银行当在编职员。他原以为县城没有内卷,工作比较清闲,可以把房间布置得很温馨,每天晨跑,还养条狗。然而,现实并不如此。硕博毕业生涌入县城似乎成为了新趋势,但他们过上想要的生活了吗?他们真的甘于待在小县城里?最终有没有实现到内心的安置?
上海封控两个多月后逐渐松动,许多人动身离开这座城市,但离开并不容易。阿森是一位“骑士”,最近成为了免费摆渡人,接送想要离开的人到车站。他认为,人们绝对想像不到人家一心想要“回家”的那种感觉,同时在摆渡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假如顺利,他也打算在5月底回家。
想回家的还有60岁的黄建才。妻子数月前从江苏常州来到上海化疗,5月初不幸病逝。黄建才认为千万不能让亡妻一直在外面漂着,于是拖着装有亡妻骨灰的行李箱,排除没有公共交通、不懂网上买车票等困难,徒步克服长达七个小时的路程来到虹桥站。逢桥遇水,他会放慢脚步,按照常州当地习俗,在心底呼喊着引领妻子的亡灵过桥:“殷桃香,哥哥带你回家。”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5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看看城里的人有多想出去,又怎样出去。
硕博生涌入县城之后
出品:人物

图:视觉中国
“北京不缺我一个打工人,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与县城也格格不入。”青柠(化名)是北京某金融专业硕士毕业生,目前却在山西老家县城某银行当在编职员。
银行秋招开始时,青柠的唯一念头是留在北京,投的大多是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公司。现实是北京的金融圈“太卷”了,光是简历关就需要人脉,但青柠的本科不在北京,原生家庭也无法给予支持。两三个月里,他参加了89场面试,每次结束都只能在 word 里敲下一句话:“今天面试未果。”
因此,当山西老家县城某公司抛来橄榄枝,青柠高兴坏了,感觉是“飘萍终于有了归处”。然而,他后来发现自己的心理预期过度美好:“我觉得这里应该没有内卷,工作也比较清闲,我可以把房间布置得很温馨,每天晨跑,还养条狗……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硕博毕业生涌入县城似乎成为了一个新趋势。他们都受过最高等的教育,部分人甚至毕业于最好的大学,也在最大的城市里见过世面,如今却挤进县城,下街道、入乡镇,在银行、中小学竞争那些“基层”岗位。
有人认为这是人才浪费,也有人认为这种趋势没有什么值得奇怪。年年扩招之下,硕博生已经从稀缺变成供过于求,可选择工作领域也相对变得狭窄。另一方面,离开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去小县城找一份安逸的生活,也是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新趋向。
然而,扎进县城里的硕博生真的过上想要的生活了吗?他们真的甘于待在小县城里?最终有没有实现到内心的安置?
《人物》找到了多名去县城的硕博毕业生,他们基本涵盖了年轻人最热衷的体制内身份——公务员、在编银行员工、教师等,还有一位“非体制内”的、回县城创业的海归硕士。他们讲述了选择县城的理由,以至于在县城里的生活和工作到底是怎样的。
疫情之下,一个男人决定将亡妻的骨灰带回家
出品:澎湃新闻

图:巩汉语、邹佳雯 / 澎湃新闻
32年前,黄建才带着殷桃香到上海买东西。东西买完,俩口子就回家结婚。两个月前,妻子带着一个红色行李箱,从江苏常州来上海化疗。5月6日,她病逝于上海。
此刻在上海空荡荡的街头,60岁的黄建才拖着那个红色行李箱,只知闷头往前走。箱子里装的,正是亡妻的骨灰。当务之急,黄建才想尽快把亡妻带回家去:“不能让她一直在外面漂着。”
疫情之下,黄建才没能叫到去虹桥站的车,也不懂怎么抢票,就把抢票的任务交给儿子、儿媳、侄女等,自己直接动身,从位于老闵行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闵行分院,一路走向虹桥火车站。
虹桥站每天只有一班车能到常州,一票难求。黄建才顾不了这些,总不能一直等着,先到车站再说。5月7日下午一点,黄建才拖着行李箱已经徒步七个多小时,走了20多公里的路。一路上,他几乎没有停下,只有在碰到过桥的时候才放慢一点脚步。按照常州当地习俗,亡灵自己过不了桥,逢桥遇水便需要黄建才在心底呼喊引领:“殷桃香,哥哥带你回家。”
我,19岁,在上海免费送人去火车站
出品:每日人物

图:人民视觉
上海封控两个多月后逐渐松动,许多人动身离开这座城市。那并不容易,从上海发出的列车有限,幸运的人才能抢到一张宝贵的车票。公共交通也没有完全恢复,为了去到车站,有人花钱坐高价车,有人骑共享单车,更有人拖着行李走了一天。
刚满19岁的阿森是一位“骑士”,住在通往虹桥站的北翟路上。5月1日,被封了一个月的阿森得以复工,一周后成为了免费摆渡人。最初,他只在回家的路上接送离沪人士,后来接送路程越来越长,最长的一次骑了70公里。他还组建起微信群,聚集了50多位愿意免费接送人们的骑手。
“太想回家了。”一位湖南大哥对阿森说。大哥早上七点便从宝山区出发,独自走了一整天,行李包括一个很大的箱子、一箱瓶装水、一些吃的,还有一个帐篷和一张被子。阿森一个人拉不完这么多东西,只好叫朋友过来帮忙;因为行李太多,骑车都骑不了,只能硬走。大哥说,他其实还没买到车票,只想在虹桥站上蹲着,买到票就立即走。
阿森认为,人们绝对想像不到人家一心想要“回家”的那种感觉:“没票,他都要去虹桥。没车,他宁愿走去虹桥。你来路上看看,一个个都拖着箱子往虹桥赶,有的人四个轮子都拖坏了还在拖,就想赶紧回家。”
本轮疫情的3个月经历,让阿森觉得自己成长了,除了年龄还停留在19岁,其他什么都变了:“我预计在5月底回家,到家之后,吃个饱饭,再念念经,养养心态。”
漫长的告别,东航“平安扣”姑娘
出品:在人间 living

央视新闻发布的“平安扣”纸条。图:新闻截图
周正鸿每天吃过晚饭都要泡上一杯茶,到女儿玉笛(小名)的坟头坐一坐。妻子苏玉芳则待在家里,刷着女儿的小视频,时不时拭去不知何时掉下的眼泪。17岁的小儿子失去最亲的姐姐,承受不了打击,脾气日渐暴躁。周家命运急转直下,始于“东航 MU5735 事故”。
“平安扣整体圆滑顺畅,寓意事事圆满,事业一帆风顺,家庭圆满幸福。”在事故搜救现场,武警官兵标记出一张边缘烧焦的纸条,上面写着这样的笔记。玉笛喜欢玉,坐飞机时会随身携带一本厚实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的全是关于翡翠的专业知识。搜救现场找到的纸条,便是笔记本的其中一页。
周正鸿是云南省昆明市滇源镇土生土长的农民。玉笛懂事,18岁便外出打工,今年从广州回到昆明,跟一家公司签约成为带货主播。工作刚一个多月,公司因应疫情而停工,准备迁去广州。玉笛和另外八位同事本来乘坐另一趟飞机,出发当天商量后才改签了东航 MU5735 航班。
4月13日,玉笛的遗骸入土为安。那是周正鸿一块砖一块砖为女儿垒成的坟墓,遗骸则只有四小根骨头和现场挖来的泥土。对周家来说,莫大的安慰是那张“平安扣”纸条,它跟玉笛的遗骸一样重要;他们希望,纸条能尽早回家。
住在“命案现场”:一个父亲的孤独
出品:澎湃新闻

姚元清现在睡的房间,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曾被公安认定为案发现场。图:明鹊 / 澎湃新闻
姚元清(化名)自小残疾,父母离异后成为孤儿。九十年代初,他花光全部积蓄在湖南省岳阳县新建村买下一套两层小洋楼,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兴高采烈地搬进来,原以为自此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没想到,二儿子姚小超在18岁那里自杀身亡,紧接着妻子病逝,因为家贫而被送走多年的小儿子姚小峰(改名:冯玉祥)更于2013年初被发现死于离家不到百米的水塘里,而被指控杀害冯玉祥的不是别人,却是大儿子姚小皇。
案子从2013年持续到2018年。岳阳县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姚小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原审定罪证据主要基于姚小皇的供述,但供述的取得并不合法,在没有目击证人、作案时间无法确定、作案动机存疑、作案工具无法确定等情况下,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间接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遂认定姚小皇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
无罪释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姚小皇变得沉默、疑心重、脾气暴躁,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总觉得有人要陷害他。由于没有找到真凶,依旧有人觉得他有嫌疑;村里有人说,姚小皇虽然出来了,并不一定就没有犯事。
如今,姚元清独自一人居住。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小洋楼也变成了老房子。晚上,他在一楼堂屋背后的房间睡觉,那里一度被公安认定为案发现场。“这里、这里……这个顶部当时都有血迹,墙壁上有明显的刮痕,公安说这些经检测都是冯玉祥的血迹。”血迹早已经干涸、变色,成为白色墙壁上的一个个黑点。
“小儿离别无物赠 / 留下一语我心肝 / 愿儿前去关煞少 / 一帆风顺把名标”当年送走儿子后,姚元清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回忆往事,他称这个决定是他永远的伤痛。他觉得很奇怪,自己从来没有梦到过冯玉祥。冯玉祥死了也快十年了,他说。
522周年祭,白银越野赛仍未完结
出品:流落南方

四届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选手号码布。图:选手提供
2021年5月22日,172位越野跑者参加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但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主办方涉嫌安排失当等因素,造成21位跑者遇难,生还跑者则要承受皮肉和心理上的创伤。
本文作者是生还跑者之一。事故周年祭之前,他到了甘肃省,想要重回当日的赛道,寻找21位跑者遇难的位置,给他们每人送去一枝鲜花。然而由于当地的疫情防控政策,行程最终无功而返。
作者认为,无论是否愿意去写,这都是一篇必须要写的文章:“因为我们从未忘记!终此一生,刻骨铭心。”
至于该写什么呢?作者不愿记述家属们时隔一年仍未摆脱的丧亲之痛,因为不希望再让他们回亿往事,更不愿由自己来揭开他们的伤疤。他愿意写当日全力救助跑者们的常生村和胡麻水村村民,但不能写,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在当地的生活。他可以写当日的其他跑者,其中几位本来就是他的老朋友,但他不愿意写大家看似岁月静好,因为他能深刻感受到大家并未走出过去。
“我们已经等了一年。”白银越野赛事故后,五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批捕,司法程序却一直没有下文,没有查到判决书,也没有媒体报道。进入纪检监察程序的两人,也没有一点消息。2022年5月22日的周年祭来临,这一事件却未完结……
消失的童哲:天才、CEO、赌徒
出品:GQ 报道

插画:陈禹
2014年创立在线教育机构万门大学以来,“降低中国教育门槛”成为了 CEO 童哲不断宣示的座右铭,就像印在他脑门上的宣言。今年3月22日,万门大学忽然暴雷,旗下应用程序再也无法登陆,并且从应用商店下架,收费用户的 vip 群全被解散。童哲至今下落不明。
万门大学贩售的,是你一生中可以接受的任何教育,从小学 、初中、高中到大学,还有成人职业技能培训。它推出过均价1.6万元(人民币,下同)的“终身学习会员”,以及再交9999元即可“学满3600小时退所有费用”的“骗局”,涉及营收总额超过6亿元。最高峰时,它拥有超过1000万名学员。
万门大学暴雷后,GQ 报道的记者走访北京和童哲的家乡厦门,探访他的朋友、前合伙人、员工、供应商、中学老师、万门大学学员等,尝试通过接近30位受访者,探寻一个曾经恰好踩到风口、怀抱教育理想的优等生,怎样走上了逃亡之路。
调查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并非一个理想主义一败涂地的故事。记者认为,当我们从旁观察每个时代最疯狂之人所做的选择,总能读懂一些新的东西——人该如何定义成功?当时代迅速变幻,人该如何及时调整自己,如何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