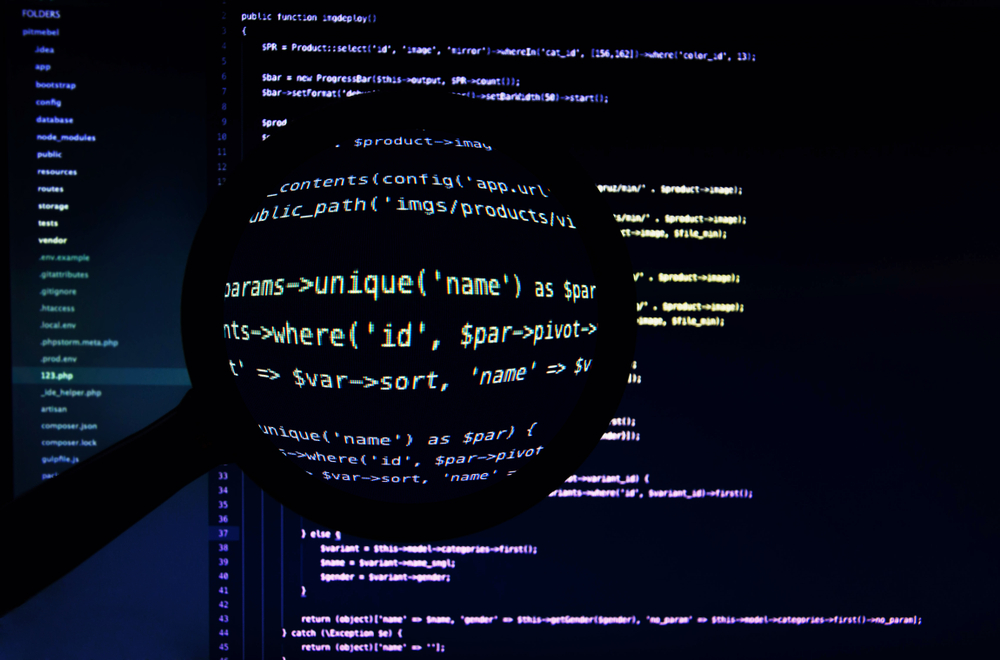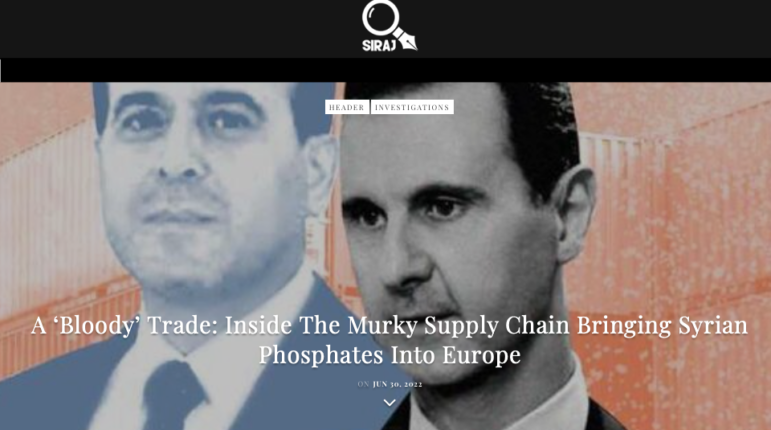在过去的25年里,我进行过最艰难的报道,是采访一些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受害人,她们作为暴力、灾难和冲突的受害者之后还会被当权者二次伤害。
例如说,一个年仅12岁的海地女孩被迫与联合国维和人员发生性关系以换取食物;一个南苏丹母亲据称在女儿面前被联合国维和人员轮奸;一个斯里兰卡学生告诉我,他被警察鸡奸得很严重,导致现在上厕所都很困难。
这些故事如此艰难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受害者没有一个人获得公义或赔偿。
在过去18个月里,新人道主义新闻社(The New Humanitarian)和汤森路透社基金会采访了70多位女性,她们表示,在2018至202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爆发埃博拉疫情期间,一些世界知名组织的援助人员通过向她们提供工作,以换取性服务。
另外,有超过40名女性声称自己遭到自称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工作人员的性剥削或性侵犯。其中一名女性称自己被强奸,另一名在堕胎后死亡。
因为我们的工作,这些救援组织已经启动了内部调查程序,英国国际发展委员会(UK’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呼吁政府打击那些接收政府资助的同时、又被指控参与性剥削的组织,一些救援组织也开始招募更多遏制性剥削的工作人员。
一个调查性剥削丑闻的独立委员会已于2020年10月份成立,调查涉及世卫组织的44项指控。然而直到今年5月,调查人员才要求我们帮助他们进行调查。
我们正在与该委员会讨论调查事宜,但最近也有其他调查人员询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和他们分享这些受害人的详细资料。
“你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这些女性,”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最近和我说,之前我曾就一项调查采访过他。“如果你们真的想帮忙,就会通过分享信息来协助调查人员。你们这样做比什么都不做还更糟糕。”
我和他一样沮丧,但是记者不是敌人。
作为记者,我们的角色是报道准确、公正的信息,作为一家人道主义新闻社,我们的角色是帮助生活在危机中的人们放大他们的声音。
但我们的职责也包括保护女性的隐私——出于从个人安全到社区内歧视风险等各种原因——并尊重这些女性自己的决定权。
作为记者,我们的工作不是强迫这些女性与他人分享被性剥削的细节,尤其是当我们不能告诉她们在公义和援助方面可以期待有些什么样的期待,或是调查将如何进行的时候。
然而,我们要确保她们被性剥削的事被写入报告,并让她们与能促成行动的当地人权组织取得联系。我们还要确保她们知道,如果愿意分享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会随时都会准备好帮助她们。
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被性剥削的女性们都还是不愿意的。
我们是如何工作的?
在过去五年对性虐待的报道中,从执法官员到援助人员,每个人都无数次地问我,作为记者,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来帮助受害者。我们会否会与联合国和其他调查人员共享联系信息?我们会带着嫌疑犯的名字去警察局吗?我们会否游说政府来推动这些案件解决?如果受害者面临威胁,我们会帮助他们重新安置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们会帮助这些受害者讲述她们的故事,并使人们对这种情况有更广泛的认识。
采访受害者通常需要几个小时、几天,甚至有时候几周时间——其中一些人告诉我们不应该把她们称作“幸存者”。
但在我们出发进行报道之前——甚至在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方法是否奏效之前——我们就计划好如何进行采访,以确保潜在受害者的安全。
我们的报道团队中有足够多的女性吗?我们需要哪些语言?我们可以在哪里进行小心的采访?我们如何帮助受害女性接受采访?当她们讲述被虐待的痛苦细节时,我们怎样做才能避免增加她们的痛苦?
一到那里,我们就花时间让倾听她们分享自己的经历,我们还会询问她们是否允许我们与调查人员或其他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例如当地的妇女协会)分享她们的详细信息。
即使她们拒绝,我们也会确保我们知道如何在未来联系到她们。这意味着在电话号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额外询问她们朋友或家人的号码,或者开车按路线多走几遍,以确保我们记住地标,以备需要时再次去拜访。
独立调查
在去年9月发表的第一份调查报告期间,除了询问她们是否愿意与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或刚果卫生部分享她们的详细信息时,我们还告诉了她们当地的一个妇女权益组织SOFEPADI。
最近,我们获知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刚组成。直到今年五月,调查人员才开始着手调查。
虽然我们准备好再次联系受害者,看看她们是否改变了与调查人员共享信息的想法——在刚果进行采访花费不菲,而且由于最近导致数百人死亡的暴力事件激增,受埃博拉影响的省份现在处于戒严状态——但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
根据专家建议,这些是我们向委员会提出的一些问题(用英语和法语),受害人在分享自己被性侵细节之前,也可能会问到这些问题。
- 调查采用的方法是什么?
- 你们有多少调查人员,他们说什么语言?
- 你们会与世卫组织或其他联合国调查人员分享这些女性的详细信息吗?
- 如果这些女性同意分享施害者的姓名,你们将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以确保她们的安全?(在刚果,被告可以在法庭上与原告对质,没有国家证人保护制度)。
- 这些女性可以从委员会的报告中期待一些什么?
这些受害女性不是孩子。她们知道她们面临的风险——报复、污名化、家庭暴力等等,她们也看到性虐待受害者获得正义或赔偿是多么的罕见,尤其是在刚果。
我同意她们的顾虑。
在近几年的报道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联合国调查是如何被搞砸的,或者需要几年才能得出结论。受害者也经常名誉扫地,亲子鉴定申请被搁置,当局也经常选择不起诉案件。
例如,一名刚果女孩据称在2017年被一名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服役的英国人强奸。尽管据报道联合国证实了这一说法,但刚果当局选择不起诉此案。
英国国家犯罪署本可以接手这个案子,但最终也放弃了,而因为该机构不受《信息自由法》的约束,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原因。
刚果当局曾信誓旦旦说,会调查我们调查中出现的指控,但人权部长安德烈·利特·阿塞比(André Lite Asebea)在5月早些时候表示,“调查没有进展”。
除了对声称为世卫组织工作的男性的44项指控之外,73名女性中有10名都指控了来自刚果卫生部的男性,这是数量第二高的指控。
负责青年和暴力侵害女性问题的刚果特别顾问尚塔尔·卢野·穆洛普(Chantal Yelu Mulop),在我们的第一份调查报告公布后不久,就安排了一次 Zoom 会议,会议的目的显然是听取更多的指控,因为其中一些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最终,刚果政府没有人响应号召,也没有人给出任何解释。我们试着跟进,但从那之后就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其他一些救援团体也受到了这些女性的指控。
再次被曝丑闻的乐施会对其在刚果的业务展开了独立调查。吹哨人指控乐施会高级职员性剥削、欺凌和腐败。在我们的调查中,一名妇女称自己被一名乐施会工作人员强奸。
乐施会表示正在向这名妇女提供援助,但即使是这个案件也引发了归责问题:被指控的施害者或者乐施会应该对此负责吗?
与此同时,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UN’s Office of Internal Oversight Services)正在调查分别针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移民组织(IOM)的单独索赔。
其他被点名的非政府组织——医疗慈善机构 ALIMA、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和国际医疗团(IMC)——也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内部调查了针对自己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指控。但他们还没有发起独立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