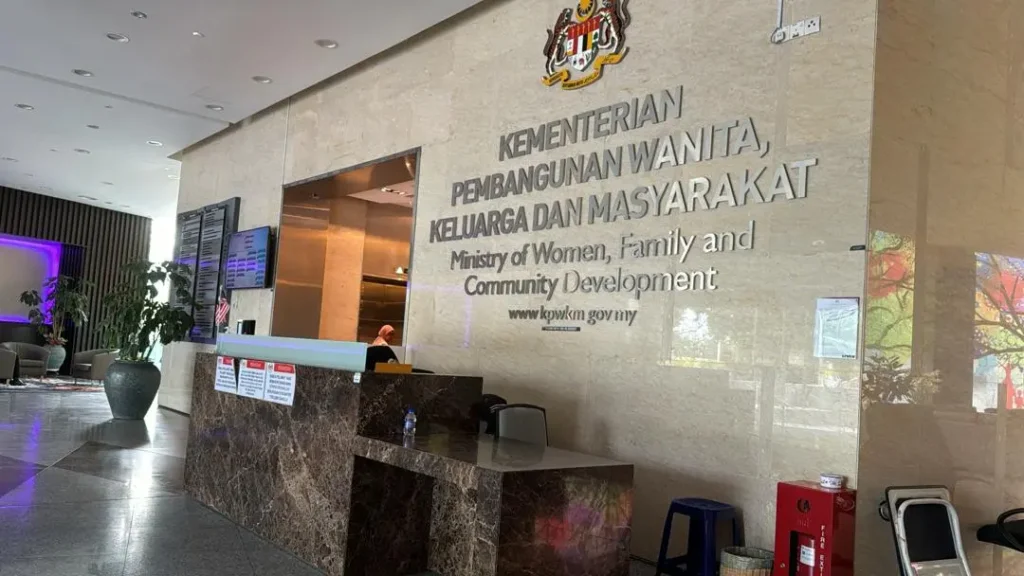“预制菜”争议、校园餐发臭,一时之间,校园餐质量和安全问题成为上海、以至全中国的热议话题。在集中供餐制之下,上海普遍中、小学禁止学生私下带饭,一些家长迫不得已想方设法,为孩子偷偷备餐。
挺过疫情、经济下行和关税,9月1日正式实行的“社保新规”,成为压跨一些小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义乌,有小厂老板决定清退工人,关停工厂。
在中国,约3080万儿童和青少年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障碍,当中不少人停学、休学。然而,不少家长并不理解孩子休学的真正原因,忽略了为孩子寻求身心治疗,反而涌入直播间,寻求让孩子回去上学、恢复正常的捷径。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9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偷偷给孩子带饭的上海家长们
出品:真实故事计划

上海浦东某学校的午餐。图:真实故事计划
在上海静安区,清晨6点,李豆厨房里的灯就亮了起来。她系着围裙,站在灶台前,把煮好的咖喱牛肉盛进保温杯,拧紧,再迅速放进儿子的餐包,就放在那个原本用来放汤碗的位置。初二的孩子就读的这所中学不允许带饭,她不能明目张胆。
在闵行区,赵南也总在清晨就偷偷给孩子备餐。她从冰箱取出一个冻得结实的保温杯,拆开新鲜的纸盒牛奶倒入杯中。这是她的小窍门——保温杯在前一夜冻透后,牛奶能在数小时内维持低温,即便是在夏天也不容易变臭;更重要的,是牛奶装在保温杯里,“别人不知道喝的是什么”。
在黄浦区,高一学生钱小熙也有自己的加餐方式。学校的饭菜难以下咽,但不得不吃。她和关系好的同学会来回走动,分享自己偷偷带来的零食。她说,甚至有男生带泡面来泡,老师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底线是别把包装乱扔。
私自带饭,被上海的大多数中、小学明令禁止,除非有医院的特殊证明。年初,李豆听儿子说,班上一个同学声称自己有肠胃炎,实在吃不下学校的菜,申请要自带一个菜,结果虽然获得豁免,依然要交每顿17元的餐费。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带饭攻防战”。面对校园餐口味不佳,甚至存在质量问题,在多种正面反馈形式无果后,家长们最终采取的行为是偷偷带饭。
9月初,罗永浩与西贝的“预制菜”之争,意外引发公众对校园餐质量的广泛声讨。9月15日,上海家长反映孩子午餐中的虾仁炒蛋发臭,供应方绿捷实业回应称“有学校反映虾仁里有细沙”,但否认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接连的争议,把校园餐推到上海、甚至全中国舆论的风口浪尖。《真实故事计划》的这篇报道,让上海几位家长与学生讲述了他们在这场“带饭攻防战”中的亲身经历。
社保“新规”落地前,小工厂老板的选择
出品:极昼工作室

陈平打算关停工厂,把剩余的货物挪到小仓库。 图:讲述者提供
立秋以来,浙江省的高温没有减退的意思,天气仍然闷热、潮湿。义乌一家日用品厂的空调、电风扇却和缝纫机、干燥剂自动包装机一起停止了运作。几天前,51岁的工厂老板陈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 清退工人,关停工厂。
8月初的“社保新规”,是他作出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疫情以来,厂子生意受到冲击,基本无法盈利,但总体还能持平。从去年下半年起,生意开始极速下行,到关停前算下来大概亏损60万元。
往年这个时候,工厂里的缝纫机从早到晚发出声响,收纳箱日产量能达到15000个。他们承接全球客商订单,箱包经由工人之手生产、压平、包装,销往世界各地。现在一切都安静下来。原本陈平打算再“熬一熬”,但看到“新规”的消息,“感觉风险太大,没有熬的必要了”。
所谓新规,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其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保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该规定于9月1日起正式生效。
这并不是一项从无到有的新规定,本次的司法解释只是对一些争议问题进行明确,统一司法裁量标准。有学者指出,政策多年前就已经对企业强制缴纳职工社保作出规定,但因近些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实际并没有严格执行、深究。
即使如此,关于社保的规定就像投石入湖,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社交平台蔓延。对于陈平这样的小微企业、工厂老板来说,每个人都得在心里算下经济账。
“休学”直播间,挤满了需要治病的父母
出品:冷杉REC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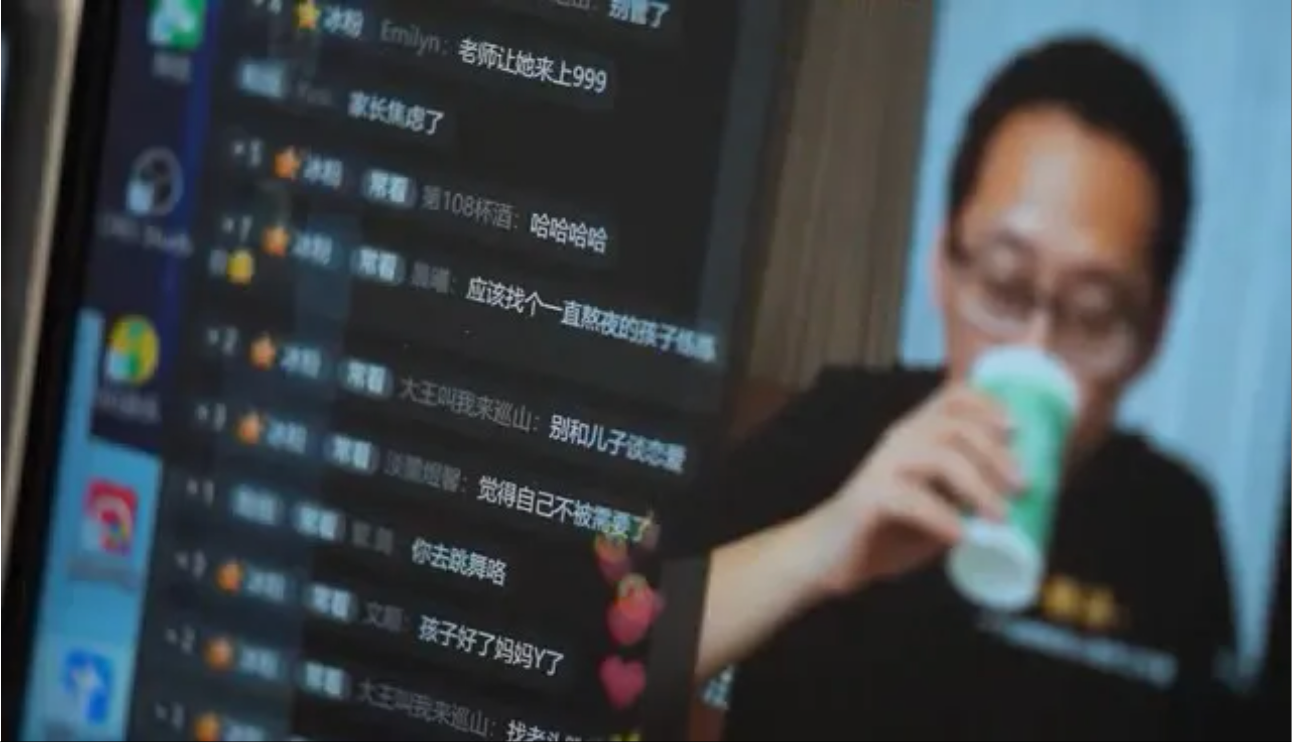
家长涌入韩冰的直播间,等待一个标准答案。图:冷杉RECORD
每年开学的第一个月,韩冰的直播间都会涌入一群“找骂”的家长。这些家长的孩子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 有的把自己锁在屋里半个月,一提上学就哭;有的在家待了两年,除了玩手机就是发呆;最长的一个已休学13年,连出门都成了难事。
情况或早有端倪,可即便发展到停学的地步,也只有少数家长后知后觉 —— 原来击垮孩子的不是矫情,是疾病。
在中国,约3080万儿童和青少年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障碍,他们是厌学、休学的高发人群。有调研显示,超过50%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经历过休学,平均休学年龄为14.16岁。照此推算,全国因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休学的孩子,或达千万之多。
韩冰太懂这种困境了。作为北京一家知名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咨询师,他有着20多年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经验,见过因父母常年吵架而拔掉头发的6岁儿童,也接触过因家长隐形控制而自伤四百多刀的11岁孩子。
在他的直播间,每天最多会有上万人同时在线,他们期待能从短短10分钟的交流中得到一颗解药,或一个答案 —— 孩子能回到学校,变得“正常”。
一场在女性腹中发生的死亡
出品:正面连接

插画:陈禹
在中国,育龄期女性(15-49岁)发生一次自然流产的风险为10%左右。全球每年发生约2300万例自然流产,相当于每分钟44例,这还不包括因胎儿发育异常造成的人工流产。
对女性来说,失去胎儿意味着孩子去世,死亡降临。与其他丧亲不同,这场死亡发生在女性身体内部。女性的身体有机会恢复,可以准备迎接下一个孩子的到来,但正因如此,死亡造成的创伤,以及告别、哀伤、悼念等人类合理的情感需求,更加容易被忽略。
女性承担着流产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她们必须服用药物,让停止发育的胚胎从子宫脱落,她们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杀死了孩子。如果胎儿已经发育成形,她们不得不把死去的孩子“生出来” —— 这被称为引产,产妇会承受超过正常分娩的宫缩疼痛,引产后同样会涨奶、分泌乳汁,怀中却没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流产过的女性,再次流产的风险会不断升高。她们越来越担心自己保不住孩子,为了保胎而打针、住院、辞职。
《正面连接》的这篇报道,访问了五位失胎妈妈。她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广州、香港、杭州等发达城市,从事教育、创作、互联网等行业。反复流产后,备孕成为了她们的生活重心。在访谈中,她们频繁提到“目标”、“成功”、“失败”等。医疗系统将女性流产定义为“妊娠失败”,这个专业术语更让她们成为“失败者”,要面临着外界严苛的审判。
更残酷的是,因为害怕失去,她们面对即将诞生的生命也更加保守 —— 不再为 TA 准备衣服,不告诉别人自己怀孕的消息,不敢觉得开心。孕育新生命带来的快乐不复存在,只剩下无尽的治疗与恐惧。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变成了试纸上的两条杠、血检单上的 hCG 值、B 超里的胎心和胎芽⋯⋯
一个较真玩家决定起诉《王者荣耀》
出品:澎湃人物

第五审判庭门口。图:受访者提供
律师孙千和是《王者荣耀》玩家,玩了八年,总想弄清楚一个问题 —— “黑箱”一样的游戏匹配算法机制是否公平?
这个疑问来自她的游戏体验 —— 对局连胜几次后,“系统好像会想方设法让你输”,比如匹配到“很菜的队友”。游戏中,时常也会有其他玩家吐槽说:“又被系统安排了。”
《王者荣耀》是腾讯游戏天美工作室群开发并运营的一款手游,官方数据称其日活跃用户数处于亿级水平。游戏圈关于这款游戏匹配算法的质疑也由来已久,却无人行动。
两、三年前,孙千和开始搜集关于游戏的算法信息,随之怀疑游戏运营方有让用户沉迷游戏,持续贡献“日活”的动机。她决定率先向腾讯公司发起挑战。
2024年6月18日,孙千和正式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起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颁令其公开《王者荣耀》的玩家对局匹配机制。2025年2月18日,法院正式立案,半年后在深圳开庭。
法庭上,腾讯方的说法,是《王者荣耀》的匹配机制旨在实现公平对战,是商业秘密,公开后易被黑产滥用。孙千和则认为,游戏里的算法机制不应该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公开是第一步,是否公平,随之也会有答案。
该案被称为“中国游戏算法诉讼第一案”,游戏匹配算法是否需要公开,在法律规定上尚属空白。
腾讯方对诉讼有成熟的应对,先后提交了超过900页的证据。作为一个足够较真的游戏玩家和从业十年的律师,孙千和为自己代理,但相比对面的律师团队,她像是“孤军奋战”⋯⋯
一名女护工逃离养老院的理由
出品:单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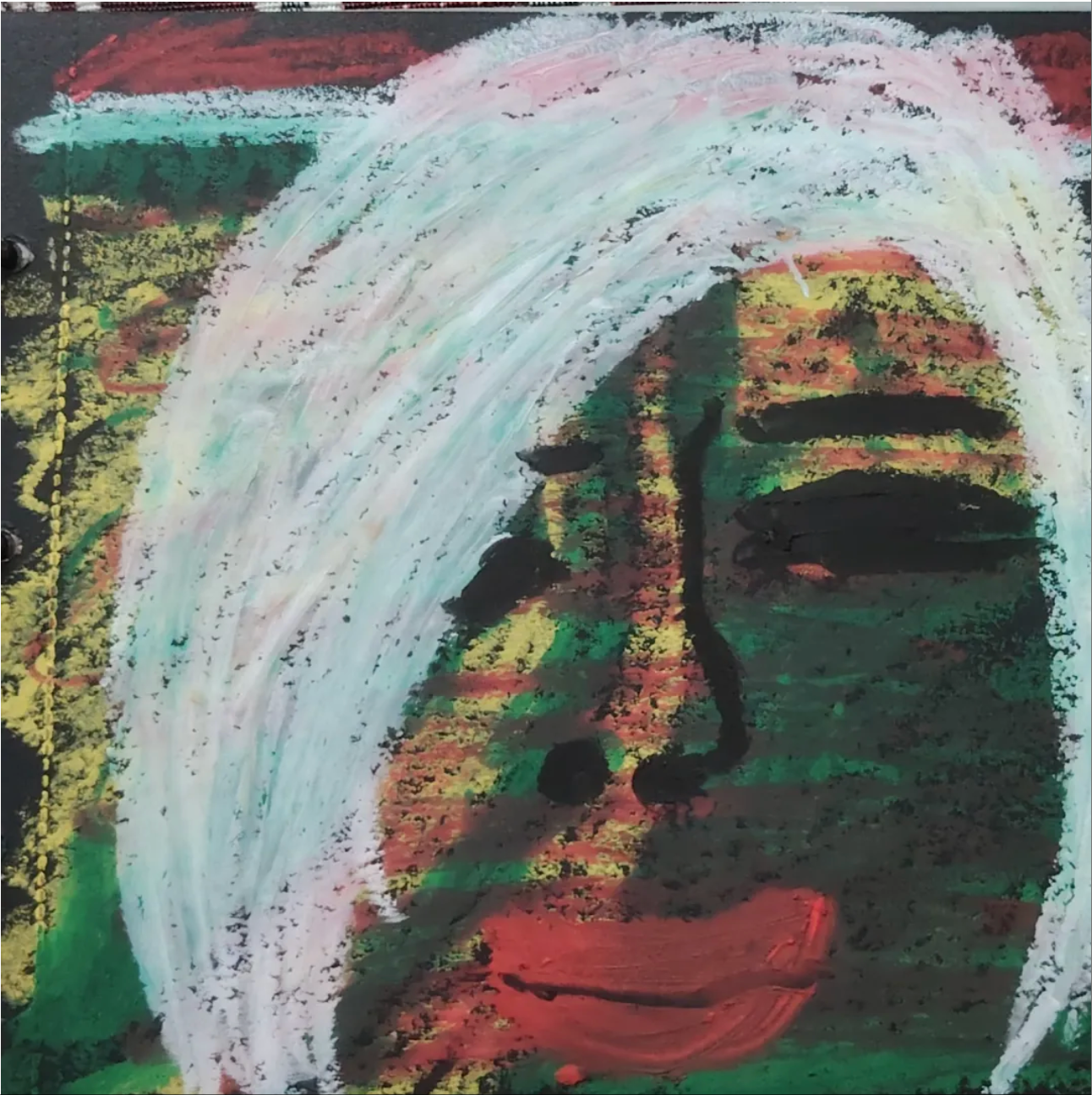
插图:李文丽
李文丽(梦雨)当过近十年的家政工,代表皮村文学小组和鸿雁之家参加了许多活动,很多人都熟悉她的故事 —— 从甘肃老家到北京打工,内向的她不仅认识了更多姐妹,还画了画、写了书。
不过,她比较少提起的,是在疫情期间去一家养老院当护工的经历,而这份工作只干了不到40天。为什么她匆匆逃离了这家养老院呢?
在发予《单读》的第一稿《逃离养老院》里,李文丽说明的理由只是“心情特别压抑和沉重”。问她具体是什么事让她下决心逃离养老院,她才说起养老院性骚扰的事,说“太难讲了”,但可以“试试看”。
于是,《单读》“在皮村”栏目的这篇文章,分享的就是这一次艰难讲述的结果。这篇以第三视角写成的故事里,既有令人难堪的真实,也有电影一般的忧郁与戏剧性。文中的插图皆为李文丽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