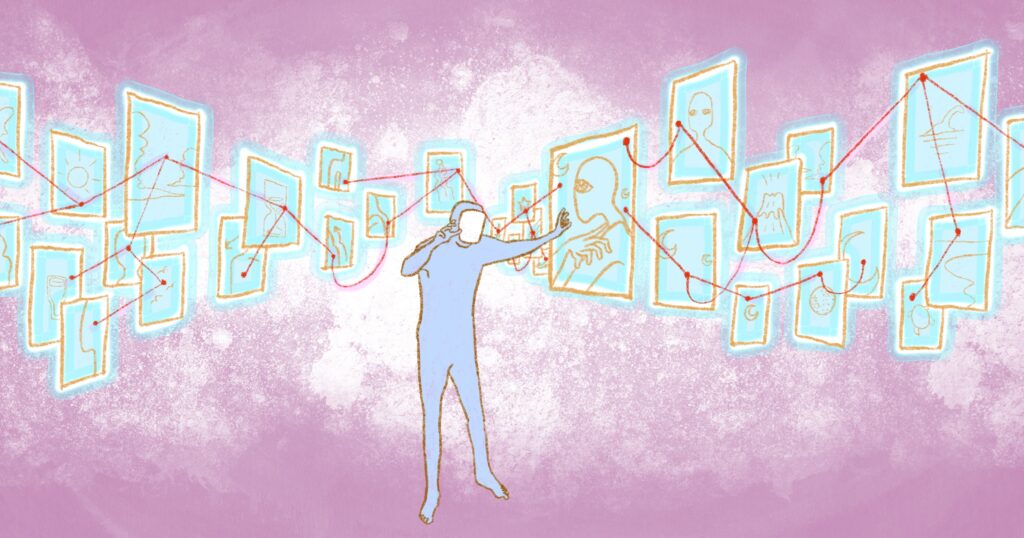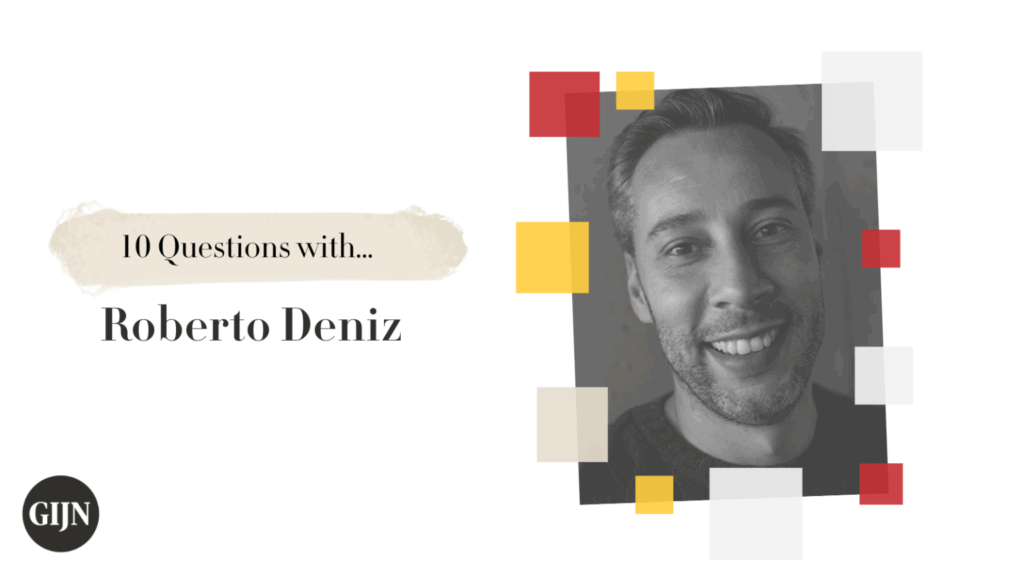近年来,环境调查报道日益受到关注。在污染、农药和有毒物质等议题尚未被视为足够“高大上”的调查素材时,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调查记者斯特凡妮·奥雷尔(Stéphane Horel)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些议题。
作为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2024年的新成员,奥雷尔还致力于调查科学领域的虚假信息传播和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在超过2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认为从事调查报道是自己本能的记者获得了众多奖项,其中包括路易斯·韦斯欧洲新闻奖(Louise Weiss Prize for European Journalism),以及因主导“永久污染”(Forever Pollution)项目而获得的2024年欧洲年度科学记者奖。此外,她还与斯特凡·福卡特(Stéphane Foucart)共同完成了“孟山都文件”调查,并因此获得了2018年欧洲新闻调查奖。
虽然她的调查工作严谨科学,但这位曾是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学生在业余时间喜欢制作拼贴画——其中一些作品还被用作她的著作封面。她在调查中采用富有创意的方法,文笔细腻,还不忘适时添加一些幽默元素。
GIJN: 在你参与过的所有调查中,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为什么?
斯特凡妮·奥雷尔: 我最喜欢的调查永远是刚刚完成的那一个,因为我的心思还沉浸其中。在“永久污染”和“永久游说”这两个项目中,我花了三年时间研究 PFAS(永久性化学物质)造成的污染问题,这个过程让我深深着迷。这是我首次涉足工业污染领域的调查,能够让这个此前如同污染本身一样无形的议题浮出水面,着实令人振奋。我们在2023年2月发布的污染地图揭示了 PFAS 在欧洲的污染程度,这迫使公众认识到工业污染的严重性,以及当前监管缺失所导致的恶果。整个团队为了公共利益而努力,成功将这个议题从环保部门的层面提升到政治和欧盟层面,这让我们感到莫大的满足。
这个项目的执行方式也令人振奋。对我来说,协调跨境调查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这就像围绕一个特定主题组建一个小型运营编辑团队:你需要让一群大多互不相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记者达成共识并投入工作,而且你与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层级关系。这既是专业上的挑战,也是人际交往的考验,但我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开创了多项新方法,尤其是如何在保持编辑独立性的同时,有效整合专家和科学家的专业意见,确保信息准确性。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专家审核新闻学”模式。
GIJN: 对于您所在的国家/地区,调查性报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斯特凡妮·奥雷尔:与在拉美或亚洲国家报道环境问题的记者相比,我觉得抱怨某些工作条件几乎有些不当。在那些地方,记者面临的风险不是应付公司的不愉快骚扰,而是可能一颗子弹就要了命。
以前被问到是否受到压力时,我总是笑着说:“从来没有,我只是在家里穿着粉色拖鞋安静地工作。”但在这次调查中——其中涉及数千亿欧元的利益,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了安全问题。有人试图闯入我家,我在咖啡馆的包也被偷……这些也许只是巧合,但我还是报了警,报社也向检察院报告了此事。这些并不妨碍我继续工作,但确实让人感到不安。
就法国的调查性新闻而言,存在着价值认同的问题。我们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调查记者协会的国家之一,这种集体性和专业性反思的缺失是一个重大缺陷。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报道文学更受重视。事实上,法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奖项阿尔贝·伦敦奖(Prix Albert Londres)就是授予这类新闻作品。在法国,人们也倾向于把调查性新闻等同于政治财经报道。因此,要说服编辑部重视其他调查主题并不容易……比如需要长期跟踪才能揭露工业污染等系统性问题的调查报道就很难获得支持。
GIJN: 作为调查记者,您遇到的最大障碍或挑战是什么?
斯特凡妮·奥雷尔: 直到最近,我研究的主题(农药、化学品接触)都不被视为调查报道的题材。2008年,当我写第一本书《大入侵》(The Great Invasion)时,这本书调查了那些污染我们日常生活的产品,但在科学圈子之外,这个话题几乎没人关注。因为这被认为是一个“消费者”话题,而且因为我是女性,我的出版商最初想做一个非常少女风格的封面。尽管我基于所有相关科学文献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但它仍被当作“女性话题”来对待。
我做了很长时间的独立记者。作为一名专注于这些被错误地认为不适合调查报道领域的调查记者,要开拓自己的道路并建立公信力并不容易。
GIJN: 您有什么采访技巧可以分享?
斯特凡妮·奥雷尔: 采访是一次交流。如果你对受访者不感兴趣,就别期待他们会说出有趣的内容。即使面对的是为农药辩护的说客,我也会试图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总是努力发现职业背后的人性。
在采访顶尖科学家时,千万不要一无所知就去问一些基础问题。这是对他们专业知识和宝贵时间的不尊重。在采访专家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课”。这种前期准备工作不仅是一种尊重,也能让你和他们进行真正深入的对话。
GIJN: 在调查工作中,你最喜欢使用的报道工具、数据库或应用是什么?
斯特凡妮·奥雷尔: 我想到的其实是一个编辑方法:幽默。用幽默的方式来处理某些议题,能够揭示出一些原本看不到的含义。
比如在 PFAS 调查中,我们整理了一份产业游说团体最具代表性的威胁言论,取名为“末日就在眼前”。其中有典型的经济要挟(“我们将不得不裁掉这么多人”),但有时候企业家的说法荒谬到令人发笑,比如一个欧洲制药行业游说组织声称,禁止 PFAS 将导致欧洲所有制药生产停摆。
幽默不仅能让报道更有趣味性,还能帮助我们抵御议题本身的沉重。毕竟,将有数十万人会因此患病死亡。如果没有幽默帮助我们保持一定距离,这种话题足以让人陷入抑郁。
GIJN: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收到过的最好建议是什么?你对有志成为调查记者的人有什么建议?
斯特凡妮·奥雷尔: 对我来说,最关键的是信任。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职业生涯中信任过我的人,因为信任就是赋能。正是因为这种信任,我才能在调查记者这条路上找到方向。
现在,当我有机会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记者合作开展调查时,我也试图回报这种信任。看到被给予空间的记者,包括一些从未真正做过调查报道的人,最终成为项目的中坚力量,带来新的视角,这种转变有时会让人感到神奇。
GIJN: 你最敬佩的记者是谁?为什么?
斯特凡妮·奥雷尔: 我非常敬佩我在《世界报》的同事斯特凡·福卡特。我们曾一起调查孟山都文件,并在2020年合著了一本关于科学虚假信息的调查报道《理性的守护者》(The Guardians of Reason)。这不仅是智识上和友谊上的相遇,也是一份感激,因为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我才能加入《世界报》。他的思维敏捷度以及不断提升高水平科学素养的能力,总是让我印象深刻。
GIJN: 你犯过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从中学到了什么?
斯特凡妮·奥雷尔: 我在实践中明白,协调跨境项目并不总是与民主划等号。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一些团队部分成员不喜欢的决定,这会产生一些需要学会处理的矛盾。为了集体利益做决定,并不意味着你就是独裁者。
在上一个项目中,我创建了一个45人的集体任务,目的是收集行业游说论据,但结果并不理想,因为有些同事不理解这种方法。这很正常,毕竟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说到底,这还是关于信任:让人们发挥自己的技能和才能。
GIJN: 你如何避免职业倦怠?
斯特凡妮·奥雷尔: 职业倦怠在我们这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普遍问题。我曾经因为工作和个人压力的双重夹击而住进重症监护室。当时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实在承受不了。虽然我热爱我的工作,到现在依然工作过度,但我已经学会警惕。我在冰箱上贴了一条提醒:“你和你的工作同样重要。”
我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是,在项目结束前的每个阶段,我都会确保每周留出一天完全不工作。统筹调查报道会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在那一天里我要么和朋友相聚,要么就瘫在沙发上看书,总之不做任何决定。
GIJN: 你觉得调查新闻工作中最令人沮丧的是什么?你希望未来能有什么改变?
斯特凡妮·奥雷尔: 跨境新闻合作和集体智慧很令人兴奋,但我觉得现在项目有过度扩张的趋势。这导致调查深度不够,却要付出过度的精力。我特别担心自由职业记者的状况,他们往往同时要进行三四项调查。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新闻编辑部,要想专注于一个调查项目几个月仍然很困难。
 Alcyone Wemaëre 一位常驻里昂的法国自由职业记者,曾在巴黎的Europe1和France24担任记者。除了担任GIJN的法语编辑,她还是里昂政治学院的副教授,共同负责新闻专业“数据与调查”方向的硕士课程。
Alcyone Wemaëre 一位常驻里昂的法国自由职业记者,曾在巴黎的Europe1和France24担任记者。除了担任GIJN的法语编辑,她还是里昂政治学院的副教授,共同负责新闻专业“数据与调查”方向的硕士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