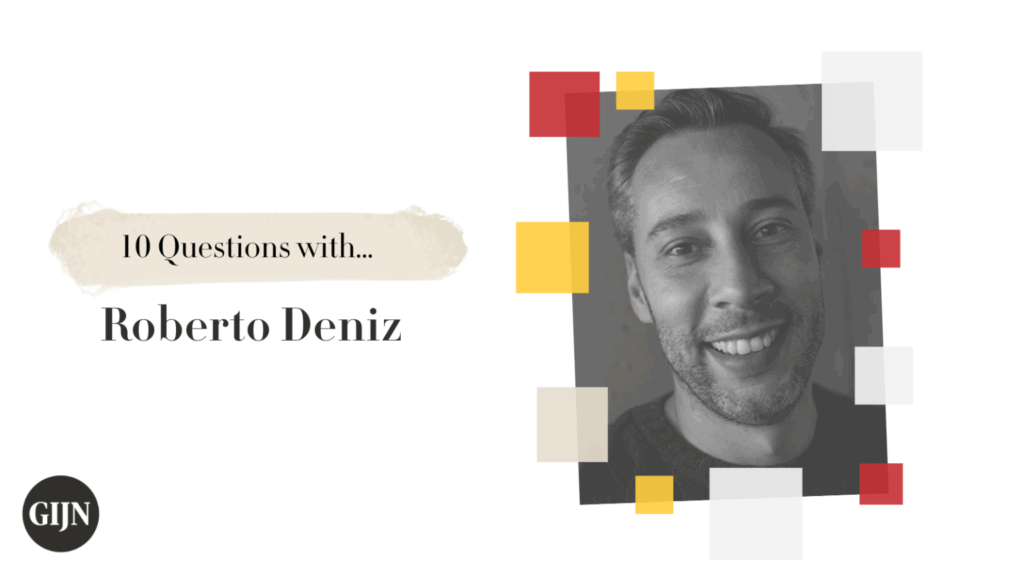插画:Smaranda Tolosano for GIJN
翻阅凯特·麦克莱蒙特(Kate McClymont)在《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档案,如同窥探澳大利亚的阴暗面:从政治腐败到有组织犯罪,从房地产丑闻到权贵丑事,她的报道常常触及那些位高权重者,或是那些不择手段、通过踩踏他人而暴富的人物。
作为《悉尼先驱晨报》的首席调查记者,麦克莱蒙特曾多次获奖。她最近制作的一档播客深入报道了一位悉尼女商人策划的庞氏骗局,这起案件最终演变成总额高达2300万澳元(约1500万美元)的特大诈骗案。

调查播客《谎话连篇》深入追查澳大利亚史上最大庞氏骗局的主谋,由凯特·麦克莱蒙特担任联合主持人。图:苹果
这档名为《谎话连篇》(Liar Liar)的播客深入挖掘了梅丽莎·卡迪克(Melissa Caddick)的故事:一个普通学生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自封的理财专家,诱骗亲友将毕生积蓄和养老金交给她投资。这些钱很快被她挥霍在奢华旅行、房产投资上,或用于满足她对名贵珠宝和奢侈品服装的痴迷。
在警方突击搜查其住所后,卡迪克随即失踪。后来她的一只脚在澳大利亚海滩上被冲上岸,验尸官最终宣布她已死亡。用麦克莱蒙特的话说,她是一个“反社会的骗子”,制造了澳大利亚本世纪最大的诈骗案。这档节目大受欢迎,也为麦克莱蒙特赢得了自己第九个沃克利奖——澳大利亚新闻界的最高荣誉。
在播客中,联合主持人汤姆·斯坦福特(Tom Steinfort)对麦克莱蒙特在悉尼有组织犯罪领域的渊博知识赞叹不已。每当他们谈到某个地方的旧案时,他总会感慨:“凯特·麦克莱蒙特,你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因为报道工作,她曾多次收到死亡威胁,面临诸多法律挑战,甚至在孩子尚小时不得不暂时躲避——不是因为报道黑手党,而是因为调查某支球队后需要躲避愤怒的足球球迷。
她1985年开始在《悉尼先驱晨报》工作,1990年左右转去做调查报道,2025年就迎来从事新闻业的40周年。她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并没有放慢脚步的打算。“当人们问‘你要退休了吗?’我就说‘不会,我会死在打字机前’,”她说,“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谢幕方式了。”
GIJN: 在你参与过的所有调查中,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凯特·麦克莱蒙特: 这很难回答。调查梅丽莎·卡迪克案件在某些方面非常精彩,因为在调查过程中你并不知道结局是什么。随着调查推进,案情逐渐展开,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我完全是偶然发现这个故事的。当时我在调查一个商人的搜查令,就打电话给负责执行搜查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问:“能告诉我你们在沃拉罗伊路执行的搜查令情况吗?”他们回答:“让我看看…等等,你说的是沃拉罗伊路还是沃兰加拉路?”因为这两处搜查是同一天进行的。他们说那是针对一个叫梅丽莎·卡迪克的人。我最初以为她与那个商人有关联,于是查了公司登记,接着就发现她已经失踪了。
我不能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调查,但我多年来一直追踪一个叫埃迪·奥贝德(Eddie Obeid)的腐败政客的故事——确实是很多年,我从1999年就开始写他。他起诉我诽谤,而且胜诉了。当时我觉得再也不能写这个人了。但我坚持下来,当他最终入狱时——现在他因为我报道的事已经两次入狱——我忍不住哭了。这个过程太艰难了,他还经常在议会里诋毁我,所以这可能是我最有成就感的调查。我不能说这是最有趣的,因为除了被起诉外,他还雇私家侦探跟踪我。这并不好玩,但能够为公众利益服务,揭露腐败并让他们付出代价,这种满足感是无与伦比的。
GIJN: 在你们国家,调查报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凯特·麦克莱蒙特: 实际上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悉尼被称为世界诽谤诉讼之都,人们动不动就提起诉讼。我曾被一位96岁老人起诉,他声称我报道他40年前的案件导致他经济损失。虽然他在案件开庭前就去世了,但我每写一篇报道都必须考虑可能面临的诽谤风险。你必须自问:如何在法庭上证实这个报道?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像警察,要考虑是否有信源愿意在法庭上作证。这些顾虑总是伴随写作过程,确实不利于报道工作。我认为澳大利亚很多媒体因此放弃某些报道,对国内新闻产生了寒蝉效应。那些富有、知名且好讼的人财力雄厚,许多机构不敢冒险,因为他们肯定会发起诉讼。
我已经被起诉约五次……而且常在发稿前收到威胁。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但比死亡威胁更可怕的是诉讼,这意味着数月的庭审和巨大压力,真的要尽量避免。
我收到过几次死亡威胁。不过我铭记一位警察朋友的话:“凯特,真正要担心的是那些不发出威胁的人。”有次威胁信直接送到我家,那是在我报道一个人在9岁孩子面前被枪杀后的一周。这确实有点可怕,但你必须把它视为恐吓,不能因此停止工作。如果被吓住,就无法做新闻。而且我觉得,杀害记者对他们来说也不明智。
在澳大利亚做新闻,考虑到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如果是在俄罗斯或南美等地区报道,我肯定没有这么大勇气。我认为那些地方的记者才是真正的勇士。
GIJN: 在从事调查记者工作期间,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凯特·麦克莱蒙特: 埃迪·奥贝德那个案子是最大挑战。在被他成功起诉后,我曾停笔半年,担心继续报道会被视为发泄怨气或报复行为。所幸最终证据确凿,真相大白。但知道有人专门雇调查员挖掘你的把柄用来要挟,这种感觉确实很不舒服。
GIJN: 你有什么采访技巧可以分享?
凯特·麦克莱蒙特: 学会做个业余心理学家。了解受访者的性格特点,选择最适合的沟通方式。我通常这样开场:“希望您能帮助我……”,尽量让对方放松、不感到受威胁。始终保持礼貌,即使对方辱骂或发火,也要冷静回应:“我很抱歉您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能谈谈吗?”
礼貌常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有时可能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关键是让对方继续对话,对话时间越长,获得的信息就越多。最理想的是面对面交谈。我明白新闻工作时间紧迫,但争取面对面交流通常是值得的。
GIJN: 你在调查报道中最常用的工具、数据库或应用是什么?
凯特·麦克莱蒙特: 我使用的是一个相当昂贵的工具。这是《悉尼先驱晨报》使用的一个程序,可以搜索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的数据,用于查询公司信息、房产信息等。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它。我甚至不敢计算自己给公司花了多少钱,因为每次搜索需要30澳元。在调查某人时,我首先想了解的是他们拥有哪些公司、与谁有商业往来、公司是否注销、是否欠税等。这个系统还能显示他们的出生日期、住址和过往的商业伙伴,这些信息能帮我逐步描绘出调查对象的全貌。
但每次搜索需要30澳元,费用会迅速累积,这也是为什么只有较大的媒体机构才能负担得起。
GIJN: 到目前为止,你职业生涯中收到的最好建议是什么?你对有志成为调查记者的人有什么建议?
凯特·麦克莱蒙特: 我认为最好的建议就是要学会合作。虽然有时我们是竞争对手,但归根结底我们都为同一个目标而工作。如果其他机构的记者向我求助,只要不涉及我正在调查的内容,我都很乐意提供帮助。要明白你可以向他人求助,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永远不要害怕提问。
由于媒体行业的压缩,我在时间上有一定优势,可以花几周时间认真完成一个报道。但对于每天应付繁重工作的年轻记者来说就很困难了。所以我经常建议他们,如果发现好的选题,可以找资深记者说:“能和我一起做这个报道吗?”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益处,因为我能传授经验,而年轻记者在其他方面也很优秀,这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模式。
GIJN: 你最敬佩的记者是谁?为什么?
凯特·麦克莱蒙特: 我最敬佩的是美国记者帕特里克·拉登·基夫(Patrick Radden Keefe)。我刚读完他的《疼痛帝国》(Empire of Pain),这本书讲述萨克勒家族(编注:一个美国经商家族,曾拥有普渡制药以及后来创立的萌蒂公司)的故事。目前我正在阅读他的另一部作品《保持沉默》(Say Nothing),主题是爱尔兰动乱时期的故事。他不仅具有出色的调查能力,还拥有极佳的文笔,这种双重天赋着实令人钦佩。
GIJN: 你犯过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从中学到了什么?
凯特·麦克莱蒙特: 我最大的失误是将两个同名人物混淆了。由于这个错误,整本书不得不销毁重印,重新发行正确版本。
另一个错误出现在一起谋杀案报道中。案件涉及一名男子涉嫌将女友推下致死,我在写作时把“米/秒”误写成“千米/秒”。一位读者来信指出:“按照你的计算,受害者都能飞到月球上了。”这完全是我的疏忽。人难免会犯错,关键是要勇于承认。发现错误后应立即向相关方报告,不要试图掩盖。要以诚相待,道歉并积极补救。
GIJN: 你如何避免职业倦怠?
凯特·麦克莱蒙特: 我今晚刚和人谈起,目前我在同时与不同记者合作五个报道,感觉每个都未尽如人意。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也在摸索解决之道。对于如何避免倦怠,我的建议是需要休息时就该休息……好好睡一觉,第二天重新出发。
有时确实会感到疲惫和烦躁,但就像今天,我在与同事合作一个报道时,从法院文件中发现调查对象竟是一个在意大利被通缉的黑手党成员。只要有新突破,工作疲惫感就会瞬间消失,重新燃起干劲。往往只需几个关键发现,就能让人重获活力,这种感觉确实奇妙。
GIJN: 对于调查新闻的工作,您觉得有什么令人沮丧的地方,或者希望将来会有什么改变?
凯特·麦克莱蒙特: 我最大的期望是能更便捷地获取法院文件和证据。我非常羡慕美国记者享有的便利条件,那里的法律体系对新闻工作者十分友好。相比之下,在这里获取案件记录或法院判决等资料始终充满困难和挑战。
新闻工作最美妙的地方在于每一天都不尽相同。回首往事,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能够从事一份如此热爱的工作——虽然不是每时每刻都那么完美——但这绝对是世界上最精彩的职业。
2023年,麦克莱蒙特凭借其杰出的新闻贡献,在澳大利亚第68届沃克利奖颁奖典礼上获得表彰(获奖感言见以下视频)
 Laura Dixon 是 GIJN 高级编辑。她曾在哥伦比亚、美国和墨西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其作品先后见诸《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和《大西洋月刊》等知名媒体。她曾担任伦敦《泰晤士报》特约记者,并获得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普利策中心和”记者促进透明”组织等机构的资助与奖学金支持。
Laura Dixon 是 GIJN 高级编辑。她曾在哥伦比亚、美国和墨西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其作品先后见诸《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和《大西洋月刊》等知名媒体。她曾担任伦敦《泰晤士报》特约记者,并获得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普利策中心和”记者促进透明”组织等机构的资助与奖学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