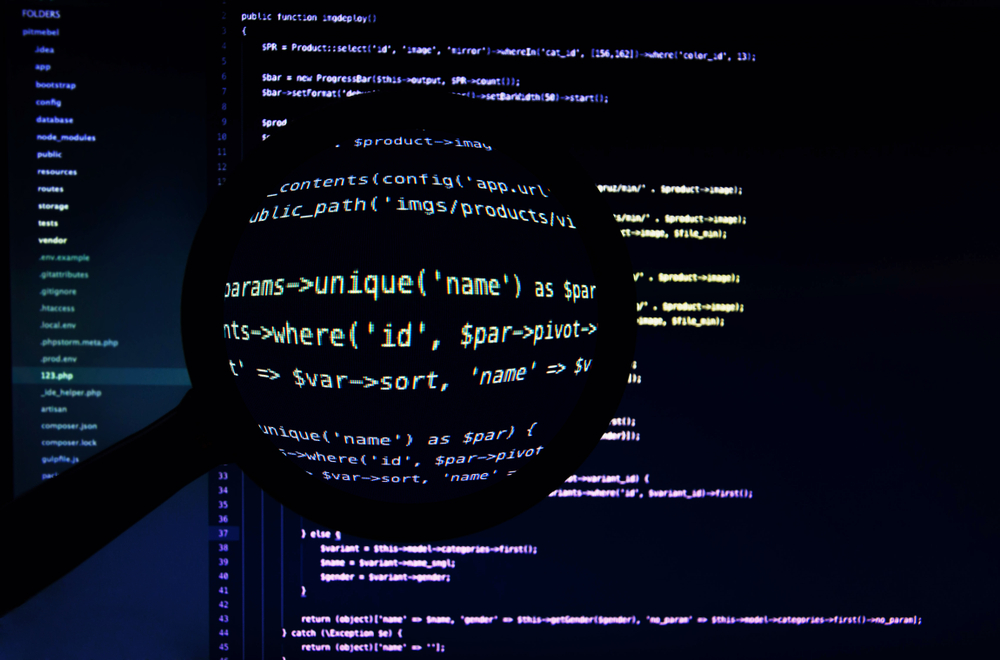GIJC23 上如何报道女性杀戮的小组讨论。图:Smaranda Tolosano for GIJN
GIJC 侧记:残缺的数据,模糊的面孔,天秤倾斜的判决——从女性杀戮报道说起
去瑞典前,我刚离开就职多年的深度报道媒体,带着一点做记者的疲惫,一点政治创伤,和很多自我探索的困惑,在上飞机前就把课表安排得满满当当。即使工作多年,我也习惯性地保持著“好学生”的样子,但其实内心并未抱太多期待。毕竟,在过去有限的交流经历中,总会听到大家说:
“China is another story.”
确实,当其他国家的同行热络地讨论着如何报道选举、如何调查影响议员和不同利益集团、如何要求更多的信息公开时,我只能讪讪地笑笑,做个安静的聆听者。
几乎每场分享,记者们都会讨论“impact”(影响力),而在中文语境中,除了一个个被算法、平台、假新闻、内容农场、不同程度的审查构筑起的信息茧房外,还有大环境的压抑与撕裂。离散和政治性抑郁成为高频词汇,离开的人不想再关心新闻背负沉重,沉重的人困在原地讲不出话。而同样是中文语境,两岸三地都有各自亟待解决的命题,不要说影响力,很多时候彼此理解都是一种奢侈。
但我还是忍不住自问:在影响力如此受限的当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和看待“impact”?或者说,如今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报道?是曲折的、触动人心的故事,还是被遮蔽的、难以发掘的信息?我在不同问题间反复横跳,直到在“报道杀戮女性(Femicide)”的分享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在有限的资源里找线索
报道 Femicide 的标签是“女性(woman)”,在踏入会议室时,我原以为会听到令人心碎或愤怒的故事,或关于二次伤害、细节披露、报道语言等伦理讨论,但令我完全没想到的是,主持人开场便介绍说,分享者都是数据记者,三个关于杀戮女性(Femicide)的项目,都是数据新闻。
过去三年受制于疫情和封控,大多时候难以到达新闻现场、甚至难以当面见到受访者,数据、开源调查成了描述现场很重要的工具和形式。然而,对于频繁使用这个工具的我而言,却总是爱不起来、恨不下去的尴尬——枯燥的数字离“人”太远,但又时常觉得信息的传达也至关重要。
因此,当听到三个项目都是数据新闻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
 其中我最有共情的是来自南非的报道 《说出她的名字:疫情中南非被杀戮女性的面孔》(#SayHerName: The faces of South Africa’s femicide epidemic)——因为他们面对的情况和我很像:笼统到只有一两个数字的官方统计,不公开的案件,难以得知被害者和凶手之间的关系,难以追查的女性被害细节。
其中我最有共情的是来自南非的报道 《说出她的名字:疫情中南非被杀戮女性的面孔》(#SayHerName: The faces of South Africa’s femicide epidemic)——因为他们面对的情况和我很像:笼统到只有一两个数字的官方统计,不公开的案件,难以得知被害者和凶手之间的关系,难以追查的女性被害细节。
事实上,南非报道团队最初的主题是性别暴力犯罪,但由于这涉及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犯罪,案情也更复杂,数据更难获取,因此他们后来锁定在“谋杀案”这样一个必定有总官方统计数据,也更单一的标准上。
为了获取更多的案件细节,他们只能通过大量检索自己组建数据库,而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南非有11种官方语言。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检索标准: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发生的,英文的,线上报道。在这个标准下,获得了482起谋杀女性案的报道,其中18岁或以上的成年女性被杀案233起。
然而,这些在媒体中有迹可循的案件,仅占成年被害女性总数(5,500)的 4%——被报道的多数是名人,或案件过于恶劣,引起社会关注。
完整的报道之外,南非的报道团队还将搜集到的近500个案件,汇总成公开的数据库,每一位被害女性都有姓名、年龄、所在地、媒体报道时间、简要的案件内容和报道来源。同时,在数据库的左上角,可以分别筛选出被现亲密伴侣杀害的、被前亲密伴侣杀害的、及被认识的人杀害的案件。
去年3月,我也做过一篇类似的报道。不过,中国的相关数据更难获取。
例如,每年分性别被杀人数没有直接的数据,只有不同年龄段的被杀死亡率(每10万人中多少人被杀),2021年的被杀死亡率要在《2022年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寻找,而这份统计年鉴发布于2023年的5月。也就是说,需要等待一年半才能得知前一年的数据,并要通过一连串计算获得。
除总体数据外,通过判决书或警方通报搜集案件同样困难重重。一是搜索“故意杀人”未必是全貌,有很多案件是以“故意伤害”、“故意伤害致死”、“过失至人死亡”等定罪或起诉;二是裁判文书网中的案件并未按照受害人性别进行区分,需逐条检阅筛选;三则是很多案件并未在裁判文书网中披露,而是地方法院、地方媒体披露在社交媒体中,或以通告形式发布在中国法院网。
一些引发重大关注的案件,甚至无法找到官方披露的文件,只能依靠我的记忆找回一些在社交媒体上的碎片。例如武汉江宸天街对疑似非性别二元者的故意杀人案,无法找到任何法律文件,没有媒体报道,最早披露事件的非性别二元网友删掉了所有相关微博,“武汉天街杀人案”等搜索词条也被微博屏蔽。
和南非记者类似的是,我也为性别暴力案件设置了不同的类别标签,分成亲密关系或熟人暴力、性骚扰、性侵和针对性别气质的霸凌等分类统计,录得的64例亲密关系或熟人暴力中,16例致死。
在数据中还原“人”
南非报道团队在现场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数据会令人觉得冰冷和遥远,只看数据可能无法调动读者的感知。因此,他们努力找到了少数愿意受访的被害者家属,通过有情感有温度的故事,串起了数据报道。

《杀戮女性:欧洲对女性的未宣之战》中用到的互动图表。
秘鲁的记者发现,法庭在判决 Femicide 案件时往往带有偏见,会用曾是亲密伴侣、被害女性不忠、伤口不在要害部位、甚至有孩子需要照顾等原因为犯案男性开脱。记者们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偏见,这份专题报道后来也发给了秘鲁的各级法院,提醒结构性不公的存在。

易小艾的报道《过去一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性别谋杀”》中的数据图表。
当时,因人员不足、时间紧迫,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没能够联系一些当事人家属,或联系在微博中做性别暴力新闻信息传递的帐号,只能独自搜集、整理、核查信息,先将检索、筛选出的东西尽我所能,跟设计和编辑同事沟通,共同呈现出来。
现在回看当时已有的材料,觉得其实可以做得更好。比如那时所纠结的案情简介要尽量少用被动句,但这也造成整篇报道看不出当事人的性别。尽量少使用被动、标题焦点放在施暴者——这样的报道伦理讨论适用于大众传媒报道的情境中,而非这样一个专门想要还原被害女性面孔的报道中。
不过如今回看,倒也没那么苛责,而是感谢那时的自己做了出来,尽管不完美,同时在看到其他国家的分享时,也惊讶地发现了很多共同点。
例如,与秘鲁的系列报道相似,我在检索中发现,“情感纠纷”、“家庭纠纷”常常出现在相关的案情通报中,甚至在辩护人意见里作为申请从宽处罚的依据——这是基于2010年2月中国最高法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而是否采纳,则关乎具体案情及当事法院法庭意见。
看到遗憾,也看到自己
结束瑞典之行后,朋友在播客中问我以后是否还会继续做记者?之后想做更有故事性、文学性的报道?还是信息翔实、角度尖锐的报道?要怎么面对好像总在对同一批人讲话这件事?
我当时说,想要做温和的、或是信息翔实的。形式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出来,更大的困境是我们在失去资料、失去历史、失去纪录。如今我也这样想,事实上,随机挑选一条去年女性被谋杀案的纪录,进行反向搜索,很难再找到原始信息。更难过的是,去年清理资料时,我不小心删掉了纪录100多条案件的更详细的原始文档。
与我同龄的记者很多都在去年、今年离职,有人读书交换,有人换了轨道,有人去写书,有人去赚钱,我们在饭桌上半开玩笑地自嘲:30岁前后是记者离职潮吧。
在并不理想的大环境里做着一份要不时燃烧理想的职业,有很多消耗和沮丧的时刻。GIJC 的会议里也有很多关于媒体存续、记者创伤的讨论。也看到过还在做记者的朋友自我怀疑时问:这些题目也不是非要我来做吧?
我想,能量很低的时候就停下来抱抱自己吧,却也不必因为当下报道见不到回音就陷入自我怀疑。布满内容农场的时代里,信息是过剩的,但有质量的信息也是匮乏的。有些记录,若没有留下,是真的会丢,若还有一些力气,就一起守住每一个留下记录的可能吧,不必在意够不够完美。共勉。
作者易小艾,独立记者,关注性别及环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