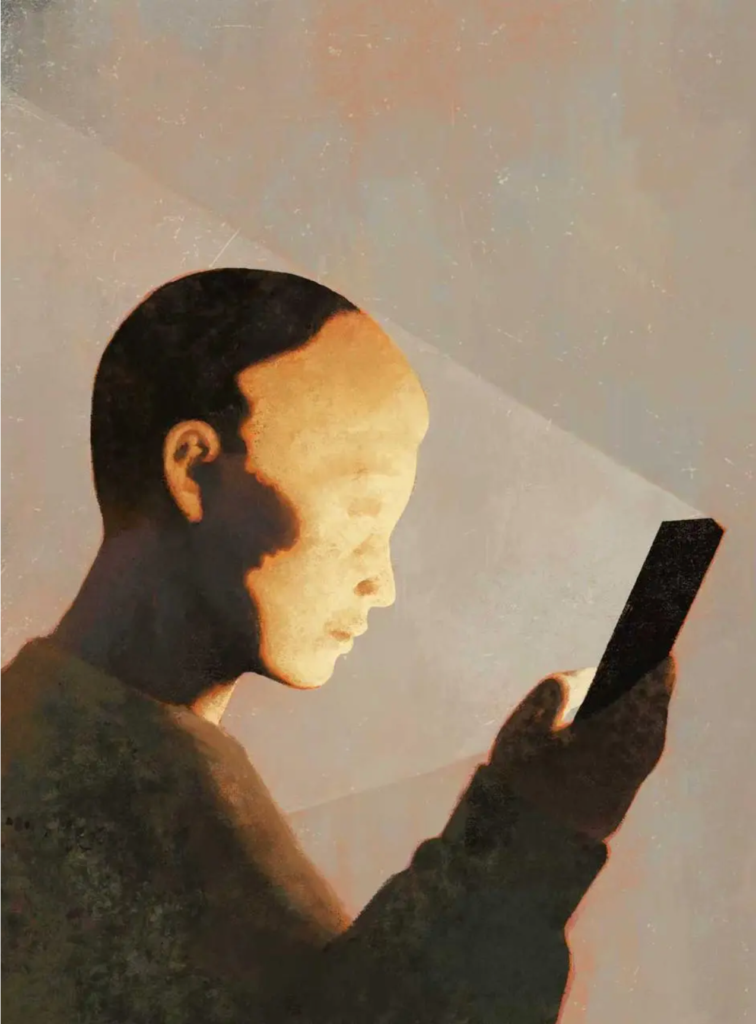從莫艾河1號碼頭位置拍攝對岸的百盛園區。圖:伍勤
2025年初,中國演員王星疑在泰國被拐騙到緬甸電信詐騙園區,幸在親友和網民號召關注和分享信息之下獲救。事件再度引起中國網絡對電信詐騙的關注,但在湄索進行田野調查的《正面連接》作者伍勤指出,跟中國輿論普遍存在的“東南亞恐懼症”不同,緬泰兩國一般人對此議題有另一種看法。
2024年底,中國當局公布第十批國家藥品集中採購結果,原研葯在本輪集采中無一中選。本輪集采迅速成為中國網絡熱話,原研葯逐漸退出公立醫院,大大影響了一部分追求原研葯的患者的就醫習慣,也迫使葯企開始轉向院外市場,尋求新的銷售通路。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1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我在泰緬邊境調查電詐產業 200 天
出品:正面連接

從莫艾河1號碼頭位置拍攝對岸的百盛園區。圖:伍勤
年初,中國演員王星疑因誤信有影視工作機遇而前往泰國,繼而被拐到緬甸電信詐騙園區,幸在親友和網民號召關注和分享信息之下,得到中國和泰國政府介入事件而獲救。相關新聞除了在中國網絡上引起關注,也在緬甸和泰國輿論持續發酵。
《正面連接》作者伍勤指出,跟中國輿論場上掀起的“東南亞恐懼症”不同,緬泰兩國一般人的情緒更多是——中國黑幫跑來泰緬邊境上搞“電信詐騙”,又拐騙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最後卻是泰國和緬甸承擔後果,兩個國家的形象在國際輿論中跟“電信詐騙”捆綁在了一起。
2023年底至今,伍勤頻繁前往湄索,在那裡從事泰緬邊境上電信詐騙產業的研究。湄索位於泰國最西端的邊境上,與緬甸的妙瓦底隔水相望,也是通往河對岸電信詐騙園區的必經之路——園區裡面無論是人,還是電力、網絡、日常消費品等物資補給都來自湄索。
田野調查期間,伍勤見證了這個行業近年來的一些關鍵節點 —— 2023年底,中泰兩國政府針對泰緬邊境電詐產業發起聯合打擊行動,救出了大量被困在妙瓦底的人。然而,事態踏入2024年後沒有明顯好轉,資本和人的流動僅停歇了一下又恢復生機。不斷有從柬埔寨、老撾的園區遷來的新公司入駐這片緬泰邊境區域,也不斷有公司遷去緬北或迪拜的園區。同時,從世界各地被騙來泰國的人依舊絡繹不絕,最終“消失”在湄索。
伍勤對園區的電詐從業者、人口販運受害者,以至圍繞着河對岸電詐園區形成的物資供貨商、司機、接待、代理、蛇頭、擺渡人等做了大量訪談。與此同時,伍勤長時期觀察這條國境線上的物理空間和賽博空間,嘗試理解“為什麼是這裡”,是什麼構成了逃避統治的基礎設施,使偷渡、人口販運和現代奴隸製成為可能。
“進口葯”退出公立醫院:這屆中產轉向民營醫院和“商保”了?
出品:三聯生活周刊

西安市第三醫院藥房。圖:視覺中國
張淼(化名)帶着患有合胞病毒肺炎的3歲女兒,驅車一個半小時,來到了深圳一家公立醫院的國際部。長途跋涉的理由,是國際部更有可能使用原研葯,而非價格更低廉的集中採購仿製葯。
張淼對原研葯的執念從懷孕開始。那時集采開始不久,公立醫院減少使用原研葯才剛出現苗頭。張淼了解到原研葯與仿製葯的概念,堅信“原研葯肯定是更好的”。孩子出生後,每次生病,醫生開藥時她都會主動要求用原研葯,但醫院很多時候都開不出。張淼的態度比較堅決,拿到開出的集採藥之後,會選擇丟掉或留着自己吃,再按照藥品名稱去藥店找同款的原研葯給孩子。
這次孩子住院讓張淼發現了新的問題 —— 雖然國際部能夠不受 DRG 支付模式約束(註:醫保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向醫院付費,不再按項目付費)而開出更全面的檢查,但在藥品上,除了抗生素等核心藥物有進口的,大部分還是以集採藥為主。住院管控更加嚴格,她悄悄問護士能不能用自己帶的原研葯,護士很為難地告訴她,要上報還要簽免責聲明,流程很麻煩。張淼沒辦法,又不甘心,只能表面上乖乖聽話,到給寶寶喂葯時,把發放的口服仿製葯換成自己在院外買的原研葯:“就像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
“我以前一直不理解去私立醫院的人。” 張淼說。這次國際部就診的經歷,讓她心裡開始掙扎,未來就醫到底要不要選擇高端私立。這讓她進退兩難 —— 相比公立三甲醫院,她並不信任民營醫院的醫療水平;但想用原研葯,似乎又不得不去民營醫院。張淼懷念以前的就醫環境:在公立醫院就診,醫生會問你要用進口葯還是國產葯,進口葯雖然會貴上很多,但每個人有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選擇的自由。
2024年12月30日,距離開標日18天後,第十批國家藥品集中採購結果正式公布。這場集采被業內稱為“歷史之最” —— 產品數量歷史最多、降價幅度歷史最大、藥品價格歷史最低。
然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原研葯在本輪集采中無一中選。六年十批集採過後,原研葯逐漸退出公立醫院已成定局,一部分追求原研葯的患者正在考慮改變就醫習慣,葯企也開始轉向院外市場尋求新的銷售通路。醫藥市場格局變化之下,民營醫院、電商平台、保險公司等相關行業,都在試圖抓住原研葯帶來的新機遇。
外賣的最後十米
出品: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

2024年12月24日,北京融科望京中心樓下,保安斥責騎車闖入的外賣員。圖:焦晶嫻
在目的地附近停好電動車後,外賣騎手還需要踏上最考驗應變能力的最後100米。一位工齡6年的騎手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總結了不少“痛點” —— 有的小區必須手寫登記,有的小區禁止騎手的電動車開進,有的老舊小區道路像迷宮一樣複雜,還看不清門牌號⋯⋯
為了節省時間,騎手們有時只能採用迂迴策略,包括自己辦理門禁卡、購買平衡車、跟保安搞好關係等。騎手們碰見不喜歡的送達地,要盡量轉單。如果是跑單高峰期,單子基本轉不出去,就“只能硬跑”。
時間限制和安全管理的矛盾,經常釀成保安和騎手的衝突。2024年12月26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北京望京街頭目睹了一場紛爭:一名物業經理試圖攔截一名騎電動車闖入小區禁行區域的騎手,該騎手沒有停下,經理上前追趕,兩人爭吵、相互辱罵,繼而升級為相互推搡。騎手試圖離開,兩名保安加入阻止,更將電動車推倒在馬路中間。紛擾直到有警察趕至,調解以騎手主動握手言和結束。“沒時間擱這兒耗。” 騎手離開前對記者說。
不少騎手從群聊里獲知了此事,接受採訪的騎手分為兩派,一派憤憤不平,另一派認為沒必要:“都是打工掙錢,吵也沒用,吵半天超時還是你的(責任)。” 有人建議和保安遞煙、混個臉熟,碰上好說話的保安就能免去登記。
為了化解一些小區管理和騎手的矛盾衝突、便利騎手送貨送餐,多地街道社區聯合外賣平台和物業公司開展“騎手友好社區”行動。深圳市物業協會副秘書長張紅喜認為,解決這些難題,除了紀律和處罰,更要“從人性出發”。
遭遇職場性侵後,我決定申請工傷認定
出品:北青深一度

崔麗麗的診斷書。圖:受訪者提供
40歲的崔麗麗在中國某家汽車零部件製造公司擔任營銷總監,在2023年的一次商務宴請酒局後,遭到了上司王某性侵。2024年4月,法院對該性侵案作出判決 —— 王某因強姦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而且要賠償崔麗麗因性侵導致的精神治療費3000元。
儘管打贏了官司,崔麗麗仍然覺得自己的權利未得到完全保護,包括公司以“未遵守公司請假制度且無故曠工”為由將她辭退。她決定繼續追究公司的責任。
與此同時,崔麗麗遭遇性侵後出現了嚴重的抑鬱、焦慮癥狀,並且被確認為創傷後應激障礙。崔麗麗認為,她需要一份《認定工傷決定書》,以證明自己在工作中受到了傷害。不過,認定工傷的過程困難重重。她先後經歷了更換醫院診斷、認定被中止、重新進行鑒定等數次波折。令她痛苦的是,她要在陌生人面前一次次講述自己的遭遇,揭開自己的傷疤。經歷九個多月的奔走,2024年12月3日,她才終於收到了人社局出具的工傷認定書。
崔麗麗說,這份認定書維護了她的尊嚴。目前,她正在整理訴求,為爭取工傷待遇提起勞動仲裁,據悉仲裁將於2025年1月21日開庭。
中學老師入職三個月被舉報 誰在監控我的微博小號?
出品:極晝工作室

一所學校公開的舉報電話。圖:視覺中國
28歲的孫依(化名)是江蘇某中學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入職不到三個月。直到接到停課通知,她才知道自己被舉報了。
2022年末的某個周三傍晚,黨委書記、副校長、教導主任坐在會議室里,對孫依逐字念着那封針對她的匿名舉報信,“罪名”被一項一項羅列出來。首先是在網絡上發表不當言論,證據來自孫依的一個微博小號;小號就像是私人日記,她在上面記錄生活,也吐槽工作。其他罪名還有“看不起同事,不團結同事”、“辱罵學生”,就連在運動會上沒拿到獎,也被扣上了“組織能力差”的帽子。每一項“罪名”底下都會附上她的微博截圖。
“這就是人家的證據。” 她無法認可:“我只是有這麼一個臭毛病,愛在網上記錄東西,但我私下的情緒從來不會帶在辦公的場合。”
學校直接給下停課處分,而且沒有定明期限。孫依試圖辯解,但校方沒有給她機會。那份人事決定已經被蓋上紅戳:“這是來通知我的,不是讓我解釋的。” 就在被處分的半個小時前,她還主持着一堂校級戲劇選修課,給學生示範表演方法。被舉報之前,她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不滿的信號,不管發任何通知,班級群里家長都是一連串的大拇指和玫瑰花,“都很有禮貌,沒有任何一個人表面上對你提出不滿。” 在那間被審判的會議室里,孫依感受到了屈辱和難堪:“你就是透明人,所有的隱私都沒了。”
在教師的圈子裡,遭遇類似不實或者不合理的舉報,並非孫依獨有。舉報通常來得很突然,還帶有隨意性。近年來,“師風師德”被說成是教師隊伍“建設”的重要一環。2019年以來,教育部至少通報93起違反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典型案例,包括體罰學生、性騷擾學生,補課收費、收受禮金等行為。隨着師風師德制度體系的完善以及“雙減”政策開展,舉報成為一種長效的監督機制,逐漸被普及。
與此同時,舉報也變成一些人謀利、報復的工具,出現擴大化的趨勢。2024年10月,《半月談》雜誌發表文章稱,2024年1月至8月,西南某教育局共收到128條舉報教師的信件,只有7起屬實。越來越多的普通教師,困在自證清白的無奈循環里。
2024年出生人口止跌回升,中國人是又愛生了嗎?
出品:穀雨數據

圖:穀雨數據
2025年1月17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人口經濟數據。數據指出,2024年的中國出生人數為954萬,同比增加52萬,扭轉了2017年以來出生人數持續下滑的趨勢。
中國出生人數止跌回升,讓不少人出乎意料。有人搶着給出答案:趕上龍年,人們想多生幾個“龍寶寶”。然而, 《穀雨數據》回顧中國出生人口數據紀錄,發現2012年龍年的出生人數是1635萬,相比前後兔年和蛇年的出生人口沒有明顯優勢,而2000年龍年的出生人數是1771萬,跟1999年兔年的1909萬相比甚至有明顯跌幅。當然,2000年龍年和2012年龍年,計劃生育政策仍在執行,大多數新生兒都是一孩。即便有家庭想趕上龍年生育二胎、三胎,也會受到政策限制。不過這至少可以證明,從一孩家庭的數據來看,生肖並未對人們的生育年份產生明顯影響。因此,即便說生肖因素存在,那麼,這也是一個相當次要的因素。
報道指出,相比於“龍寶寶”的寓意,更影響中國人生育模式的其實是時間與節氣。報道引述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王丹寅等學者指出,中國人的生育節奏與歐洲與北美明顯不同 —— 歐洲國家的生育高峰出現在一年之初,之後逐月遞減,美國的生育低谷則出現在春季(通常為四月),之後逐月遞增出生人數,這分別跟歐美的節日、公共假期、氣候等有關。至於中國,生育高峰通常在10月至12月,一個重要原因,是相當一部分中國夫妻的協作模式是候鳥型的,也稱之為“通勤婚姻”,成婚後一旦有明確的生育規劃,最合適相聚的機會便是春節假期。
問題是如果想要在2023年生育,那麼最適合生育的時機理應是2023年的春節。然而,那時候仍然處於新冠疫情傳播的狀態下,對於需要慎重養胎的育齡婦女,人們主觀上還完全沒有做好準備。“備孕需要做些什麼準備”這個搜索詞,曾在2023年春節前的幾個月內,創下近年的歷史搜索新低。
另一方面,根據山東大學、山東第一醫科大學學者發表的一份研究,相比於2022年6月,2023年3月的中國男性精子質量整體下降。這意味着,當時的新冠感染會在中短期內降低男性生殖能力。因此,疫後稍作休息,2024年成為了理想的時間,春節受孕、冬季生育,中國人的生育節奏又這樣延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