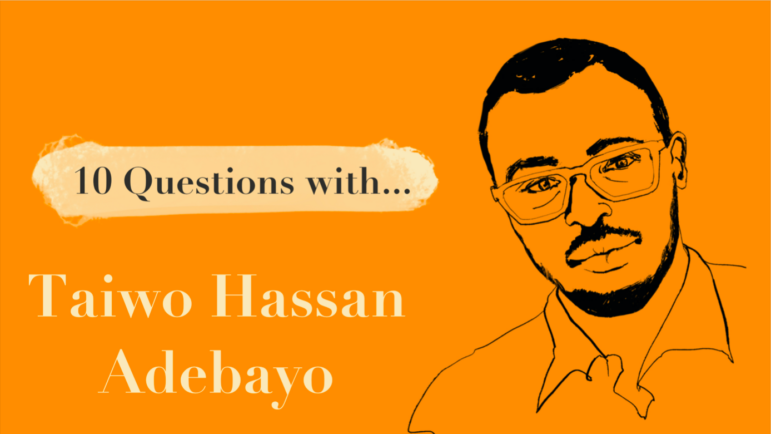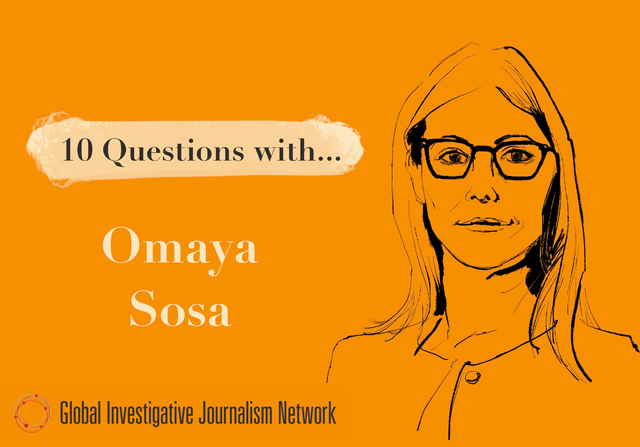林寶英(Boyoung Lim)從一名警察轉行為調查記者,再到成為普利策中心人工智能問責網絡(Pulitzer Center’s AI Accountability Network)的負責人,這一職業軌跡既非線性發展,也非事先計劃好的。
林寶英畢業於韓國警察大學,從調查網絡犯罪的工作開始起步。她說,與大多數其他犯罪活動不同,網絡犯罪需要與海外執法機構及私營部門進行大量的跨境合作,這為她後來在韓國非營利性調查新聞機構“打破新聞”(Newstapa)從事的調查記者工作積累了必要的技能。
(實際上,林寶英最初是申請該媒體的一個行政職位,“只是想看看新聞編輯室是如何運作的”,但在 Newstapa 了解到她的技能後,向她提供了一個調查記者的職位。)
在“打破新聞”,林寶英參與了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等網絡的跨境合作,報道了像“植入件檔案”(Implant Files)這樣的故事——這是一項關於醫療設備監管不力的調查,與德國公共廣播公司 NDR合作完成。「假科學」工廠(Fake Science Factory)揭露了韓國學者如何使用虛假會議和出版物來強化他們的專業形象,並用納稅人的錢去進行公費旅遊。
如今,林寶英領導着普利策中心人工智能問責網絡,該網絡提供培訓和報告資助,幫助記者報道人工智能領域,同時也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報道。她表示,自己一直熱愛調查工作——無論是作為一名警官還是一名記者。她在目前的職位上,通過支持記者獲得資金和專業知識,以人工智能和算法來輔助調查,她認為這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
在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GIJN 十問”欄目中,林寶英坦誠地分享了她如何克服從警官到調查記者轉變過程中的冒名頂替綜合症和職業倦怠的。
GIJN: 在你參與的所有調查中,哪一個是您最喜歡的,為什麼?
林寶英: 我參與過的最有趣的項目是我在 Newstapa 工作時的“假科學”調查。我們與 NDR 合作,NDR 發現了幾個在騙子期刊上發表文章的韓國名字,我們的調查揭露了韓國頂尖大學的學者和學生(信不信由你,包括朝鮮和韓國)如何使用假會議和期刊來誇大他們的學術成就,同時產出低質量的研究。
為了向我們的讀者展示這是如何運作的,我們的團隊向其中一個會議提交了一篇充滿胡言亂語的、自動生成論文。然後,它竟然被接受了!這就是他們的商業模式:只要你支付費用,你提交的任何內容都會毫無疑問地被接受。他們不在乎你是否出席會議。有些參會者甚至不會去參加實際的會議,而是選擇去意大利、威尼斯這樣的城市觀光。問題在於,這些韓國學者大多數是使用政府資金,即納稅人的錢去參加這些會議的。我們發現相當數量的學者在向韓國國家研究基金會提交的資助報告中,將這些會議列為成就。這個故事震動了韓國學術界,並激起了關於研究倫理和績效評估標準的討論。
GIJN: 在韓國,調查報道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林寶英: 在韓國進行調查報道面臨的最大挑戰有兩方面: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從針對調查記者的法律行動的武器化,到由於財務限制而導致大多數新聞編輯室降低調查報道的優先級。
2023年9月,我的前新聞編輯室 Newstapa,韓國最主要的獨立調查新聞編輯室,因為被指控誹謗總統而遭到檢察官辦公室的突擊搜查。Newstapa 還報道了時任總統尹錫悅任職前的醜聞,當時他是首席檢察官,並且牽涉到第一夫人的一宗案件。
此外,今年早些時候 Newstapa 和民權團體成功起訴檢察服務機構,要求公開特殊活動費用預算,這筆經費在以前從未被公開過。這場旨在讓檢察官辦公室對納稅人負責的法律戰鬥持續了三年,我可以想象,這一切讓那些掌權者感到非常不舒服。韓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國家機關卻公然決定將法律行動作為對抗記者的武器——而這些記者正是為了民主制度而問責權力,並且只是在盡自己的職責——這是令人遺憾的。
在經濟方面:從我在其他韓國記者那裡聽到的情況來看,當新聞編輯部面臨財務問題時,調查報道預算是首先被削減的。人們似乎缺乏對調查和問責報道在民主制度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認可。幸運的是,仍然有一些希望——越來越多的記者正在探索用非營利和其他替代財務模型來支持調查工作。例如,Newstapa 通過 Newstapa 新聞學校 提供關於調查報道技巧和如何運營非營利新聞編輯部的課程,來孵化獨立調查新聞編輯部。這個項目成功孵化了一個本地的調查新聞編輯部。Newstapa 有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通過這一項目建立100個獨立的調查媒體。
GIJN: 作為一名調查記者,你遇到的最大障礙或挑戰是什麼?
林寶英: 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感覺自己像個冒名頂替者。我埋頭苦幹,試圖彌補自己在新聞學教育方面的不足,想證明我自己配得上在新聞編輯室的位置。
有時候,我配不上現在職位的感覺會嚴重,以至於我在周末還在自責,不斷逼迫自己更加努力,不允許自己好好休息,會認為自己不配休息。我無法欣賞自己職業軌跡的獨特性。冒名頂替綜合症是燃盡症候群的最佳搭檔,我深受其擾。回想起來,我不應該聽從內心的懷疑聲音,應該更加認可自己。
GIJN: 你在進行採訪時有什麼特別的技巧嗎?
林寶英: 在採訪前,我總是覺得以下幾點特別有用:
- 閱讀關於相關人物或話題的所有資料
- 列出核心問題和次要問題的清單。
- 開始採訪時,不要立刻深入核心問題。你不會想上來就把受訪者嚇跑。
- 人們喜歡被傾聽。真誠地傾聽,就好像你的受訪者是世界上唯一的人……但你要驗證他們所說的一切。
GIJN: 在你的調查中,你最喜歡使用哪個報道工具、數據庫或應用?
林寶英: 這真的取決於調查的類型和主題。我一直最喜歡的工具是老式的筆和紙;電子表格;便簽;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材料。
GIJN 擁有許多有用的操作指南和資源,適用於不同類型的調查。如果有人對如何調查 AI 及其背後的人的感興趣,普利策中心為報道 AI 及其應用提供了一些絕佳的技巧和工具包。
GIJN: 在您職業生涯中收到的最佳建議是什麼?您會給有志成為調查記者的人什麼建議?
林寶英: 對我產生共鳴的建議來自我閱讀的書籍和我觀看的電影,這些書籍和電影讓我更多地了解寫作和新聞業。我喜歡一句來自安妮·拉莫特(Anne Lamott)的書《一隻鳥接着一隻鳥》(Bird by Bird)的話:“完美主義是壓迫者的聲音,是人民的敵人。它會讓你終身感到拘束和瘋狂,它是你和糟糕的初稿之間的主要障礙。”
來自日本電影《記者》:“相信並懷疑自己,超過任何其他人。”
GIJN: 你最欽佩的記者是誰?為什麼?
林寶英: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有很多我欽佩的記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你可能知道,因為他們是著名記者,受到廣泛的讚譽。但我們需要記住,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記者,他們冒着生命危險,甚至失去生命或因為做好工作而被監禁。他們可能不那麼知名或沒有那麼受到讚譽,正是因為他們恰好在一個受關注較少的國家或地區工作。
我參加了 GIJC23 的一個小組討論會,被 Zan Times(阿富汗媒體)記者的無畏工作所感動,出於安全原因,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在塔利班統治下女性記者可能會喪命,但她們仍在工作,並盡最大努力向當地人和世界傳遞信息,我被那些在這種情況下以勇氣和責任心工作的記者的故事所感動。
我們的行業沒有足夠認可那些雖然不是記者,但幫助到我們工作的人。我們應該提醒自己感激那些與我們一起工作的人——無論他們是不是記者——以及各界支持我們工作的人。
GIJN: 您犯過的最大錯誤是什麼,您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林寶英: 我深信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犯了不少錯誤,大的小的都有。然而,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心想要同時做太多事、追求每件事的完美,以及未能充分認可自己的努力。曾有一段時間,我因感到迷茫和束手無策,而難以繼續寫作。我不停地和他人比較,貶低自己已完成的成果。
我本該在不確定時,向同事們尋求對工作的反饋,而不是讓自己陷入負面循環。忽略身心健康,僅專註於工作,也是我犯下的錯誤。我們的身體不是機器,即使機器也需定期維護。最近,我有意識地努力照顧好自己,確保足夠的睡眠、健康飲食和適量鍛煉。工作並非生活的全部。我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在追求成為出色的記者之前,我們要先學會善待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GIJN: 您如何避免在您的工作中出現職業倦怠?
林寶英: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確實遭受了嚴重的職業倦怠。我們的工作有時會非常有壓力,而且長時間線的項目會讓你感到筋疲力盡。我嘗試將我的工作分解成小塊。我正在學習說“不”,以避免承擔過多超出我能力範圍的工作。
其他建議包括:為過度工作給自己設定獎勵,給自己適當的休息時間。如果我們耗盡了自己,對公眾將毫無益處。
GIJN: 在從事調查報道的工作中,您覺得什麼最讓人沮喪,或者您希望將來會有什麼改變?
林寶英: 許多人的努力使得調查性新聞和合作項目變得更為全球化,也更加酷。在 GIJN 網絡的擴展以及新興的創新和合作網絡中看到了希望,儘管調查新聞如今面臨重重挑戰。
我們還能做得更好,那就是讓這一領域在全球範圍內更加多元化和具有包容性。我非常期待看到和聽到更多關於平等的夥伴關係、基於尊重的工作文化,以及公平歸功的實踐。
 Ana P. Santos 是一名擁有超過 10 年經驗的記者,專門報道與性生殖健康、艾滋病毒和性暴力相關的性別問題。作為 2014 年普利策中心珀耳塞福涅·米爾獎學金獲得者和資助者,她報道了歐洲和中東的勞工移民問題。她的作品在 Rappler、德國之聲、大西洋月刊和洛杉磯時報等媒體發表。
Ana P. Santos 是一名擁有超過 10 年經驗的記者,專門報道與性生殖健康、艾滋病毒和性暴力相關的性別問題。作為 2014 年普利策中心珀耳塞福涅·米爾獎學金獲得者和資助者,她報道了歐洲和中東的勞工移民問題。她的作品在 Rappler、德國之聲、大西洋月刊和洛杉磯時報等媒體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