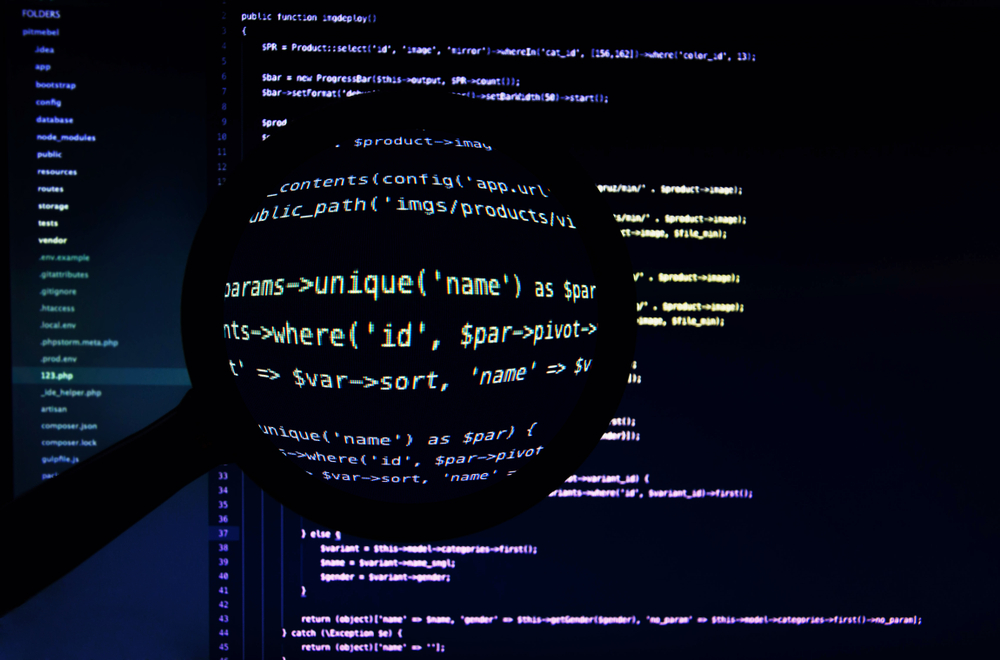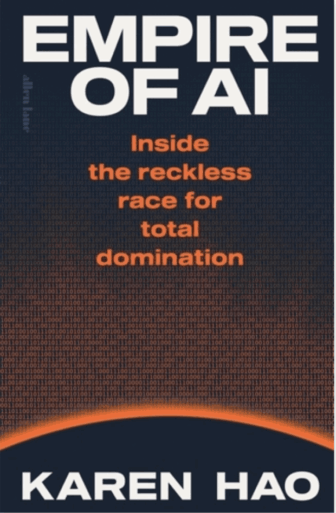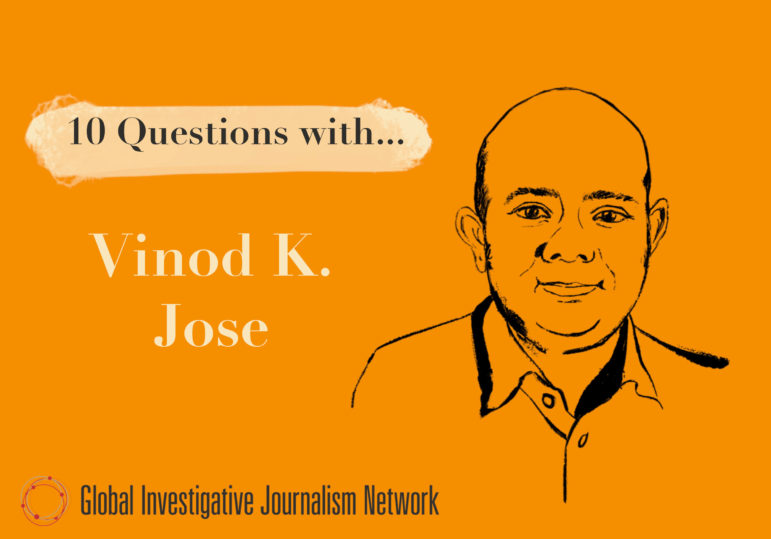Karen Hao(郝珂靈)是全球頂尖的調查報道記者之一,專註於揭示人工智能帶來的影響與潛在危害。她是暢銷書《AI帝國:從OpenAI內部揭露一場改寫世界的科技競賽》(Empire of AI: Inside the Reckless Race For Total Domination)的作者,常駐香港和美國。她率先對OpenAI進行了深度剖析,目前負責普利策中心的“AI聚光燈系列”項目,為記者們提供人工智能報道方面的培訓。
她曾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和《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人工智能高級編輯,如今她對科技發展與濫用問題的調查報道見於《大西洋月刊》等頂尖刊物。
今年11月時候,郝珂靈將在馬來西亞舉行的全球深度報道大會(GIJC25)上,作為專家組成員分享她的一些前沿見解與技巧。
GIJN:在您或您的團隊所做的所有調查報道中,您最喜歡哪一個?為什麼?
郝珂靈: 為了我的書《AI帝國》,我報道了OpenAI的內幕故事及其在全球範圍內對社會、環境和勞工造成的深遠影響。在此期間,我報道了智利各地多個原住民和環保活動團體,他們一直在努力保護自己的土地、礦產和水資源,以對抗硅谷為建設人工智能數據中心而對資源日益膨脹的渴求。這次調查是我最喜歡的報道之一,不僅因為活動家們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和精神持續激勵着我的工作,也因為我有一位出色的報道夥伴——智利天主教大學的新聞學教授 Muriel Alarcón。我們一起在智利各地奔波,追蹤信源,沿途欣賞着令人嘆為觀止的風景,整個過程充滿樂趣。
GIJN: 在您所在的國家/地區,進行調查報道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郝珂靈: 目前美國和許多其他地區一樣,媒體行業正面臨著巨大的財務壓力,這使得新聞編輯室越來越不願意投資於深度調查。與此同時,那些需要被問責的對象卻變得愈發富有和強大。就我個人而言,在調查科技行業時,我看到太多同事離開新聞界,轉而為科技公司的公關團隊工作。這意味着,我們作為調查記者,需要不斷創新,思考如何用更少的資源做更多的事。
GIJN: 在您的調查中,有哪些報道工具、數據庫或技巧很好用?
郝珂靈: 我大量使用領英(LinkedIn)、Signal 和電子表格。每次調查,我都會在谷歌表格(Google Sheet)中創建一個追蹤表,列出所有信源以及他們的狀態——我是否已聯繫?對方是否回復?採訪是否完成?——還有我的採訪筆記,有時還會記錄一些其他細節,比如我與他們達成的協議(例如,他們是匿名受訪還是作為背景信息提供者)。
GIJN: 您從同行或新聞會議上得到的最好建議是什麼?您又會給有抱負的調查記者什麼忠告?
郝珂靈: 永遠不要預設某人不會接受你的採訪。如果你不去聯繫,那這個預設就必然成真。但只要你伸出橄欖枝,他們總有可能會回應你。
GIJN: 您認為您所在的地區存在哪些報道盲點或未被充分報道的領域?其中哪些適合展開新的調查?
郝珂靈: 每一位記者,無論身處哪個地區、負責哪個領域,都有一個關於人工智能的故事可以講述。人工智能行業的影響遍及全球、跨越各個學科,正影響着數十億人,其帶來的危害往往亟需被曝光。如果你對如何入手感興趣,我與普利策中心共同設計了一個名為“AI聚光燈系列”的項目,為記者和編輯提供人工智能報道的入門課程。我將在GIJC25上主持一場研討會,我們還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免費公開所有課程資料。
GIJN: 您能否分享一次您在調查中犯過的重大錯誤或感到的遺憾,並談談您從中吸取了什麼教訓?
郝珂靈: 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不太懂得如何恰當地處理“無意外”郵件(no surprises email,在發稿前發給報道對象的郵件,通常會以要點的形式列出計劃發表的要點、一份採訪請求,以及要求受訪者回復的截止日期)。根據你所處的媒體環境,這類郵件可能適用,也可能不適用。但在它適用的語境下,最好還是發一封,並且內容儘可能詳盡。這能讓你的報道更加紮實,也有助於處理棘手的信源關係。
Rowan Philp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全球記者和影響力編輯。他曾是南非《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首席記者,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報道新聞、政治、腐敗和衝突,並曾在英國、美國和非洲的新聞編輯室擔任派稿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