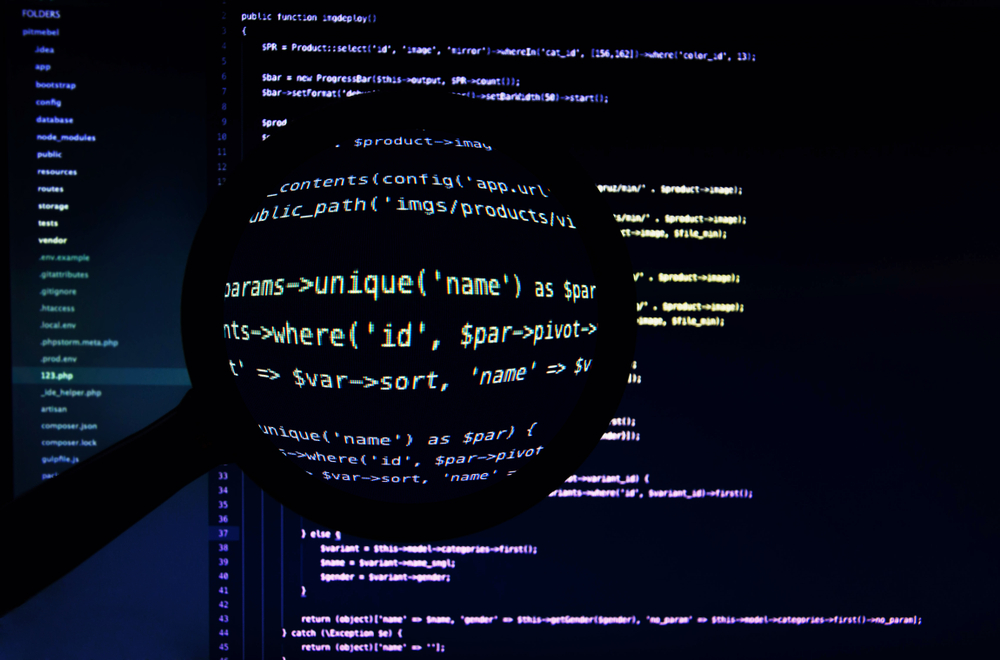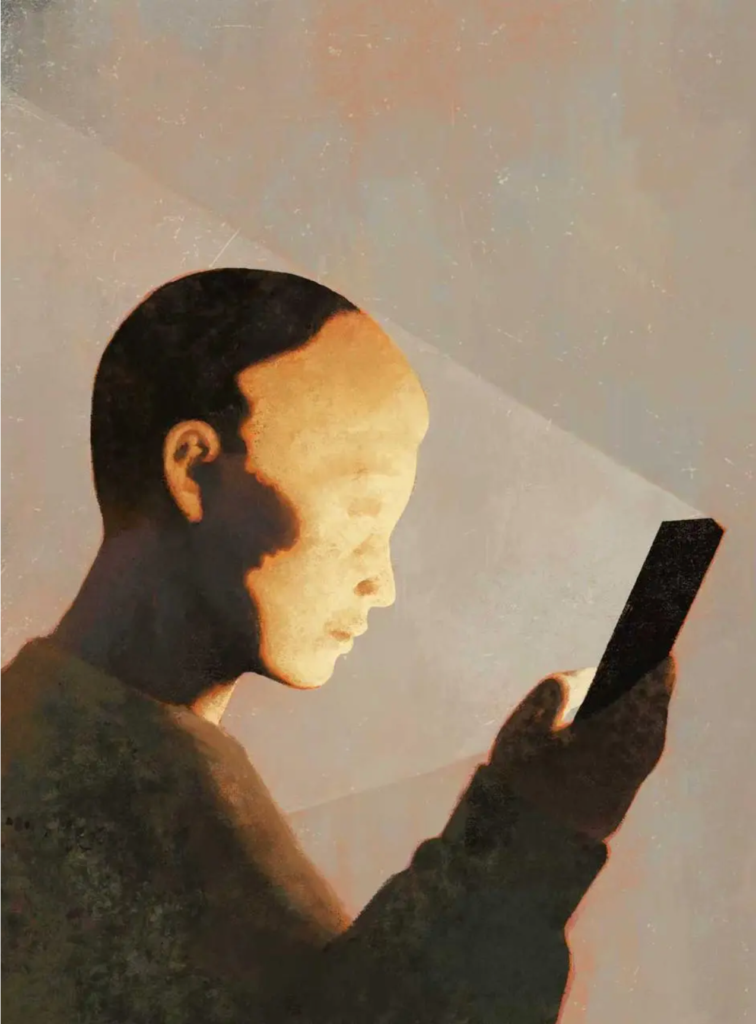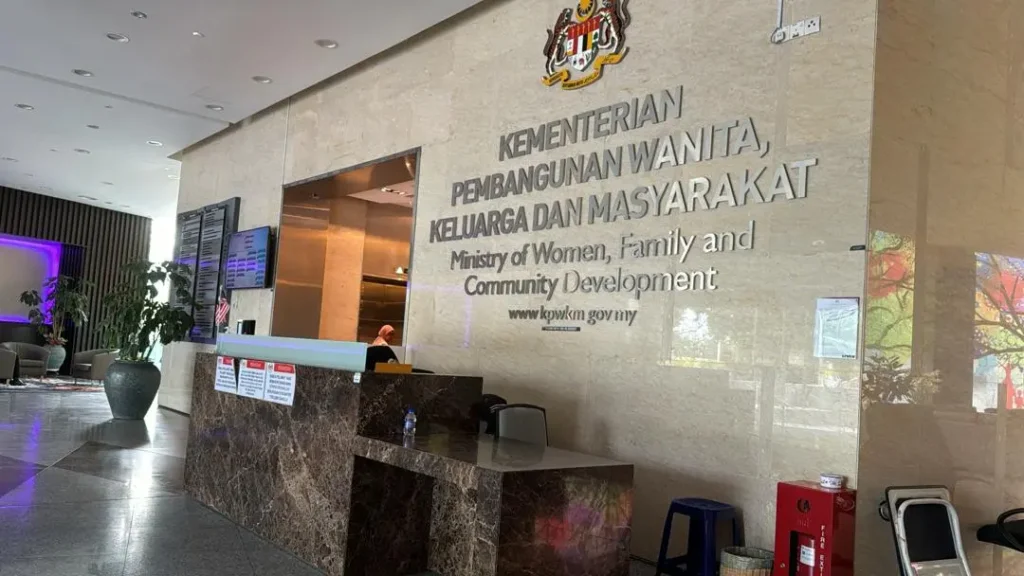在中國,關於“代孕”應否合法化,以至代孕能否幫助解決出生率低的討論持續升溫。在“法律不禁,但政府不許”的情況下,代孕一直處於灰色地帶,黑市代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民間有不少人為求子女鋌而走險,不惜跨過法外之地。
隨着中國官方近年放開生育政策,醫院的計劃生育科室不斷尋求轉型。有在科室待了18年的主任醫師表示,問診者的背景、心態和求診原因一直在改變,儘管政策放開了,大家有多生的機會,但這個機會對於每一個人來說並非完全平等的,還要看她們有沒有能力來承受這個機會。
2022年,生理性別是男性、性別認同是女性的靈兒(化名)被父母送到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被醫生診斷其存在精神問題,接受了7次 MECT(改良電休克)治療。靈兒認為,醫院在她不同意之下收治她,並且採取非必要的治療措施,侵害了她的人身權,決定提起訴訟。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9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中國式地下代孕調查
出品:財新周刊

圖:視覺中國
中國政府近年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但出生人口未如國家衛計委之前預期般增長。有學者認為,“二孩”開放得太遲,許多家庭已經承受不起再養育一個孩子的風險。國家衛計委的數據顯示,政策放寬後,育齡婦女的總量連續下降——育齡婦女總量在“十二五”期間每年減少約350萬,在“十三五”期間每年減少約500萬。高齡高危產婦的比例大幅增加,令母嬰安全保障工作承受重壓,而不孕不育率的大幅升高,更加是對出生人口比例的嚴峻挑戰。
在這個背景下,一場關於“代孕”應否合法化的討論持續升溫。長期以來,代孕在中國的定位尷尬,可謂“法律不禁,但政府不許”。中國尚未有明確禁止代孕的法律,2015年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擬“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在審議階段被刪掉,目前只有原衛生部於2001年出台的部門規章《人類輔助生殘技術管理辦法》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然而,代孕在民間不乏實踐者。1988年,中國出現首宗試管嬰兒成功降生的案例,自此代孕黑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在搜索引擎輸入關鍵詞“代孕”,可以搜出各種名目的代孕網、代孕服務,另有大批尋求代孕者、中介、代母、捐精捐卵者活躍於一些社交媒體的群組中。
中國開放代孕在短期內似乎難成現實。《財新周刊》歷時數月,設法尋訪了參與黑市代孕,以及出國代孕的多個家庭、相關中介機構、代孕母親等,儘力全面呈現他們的敘述。記者發現,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關卡解鎖後,對於不少求子者來說,要成為父母還需要千方百計跨過一片法外之地。
計劃生育科室轉型後,生育故事的一體兩面
出品:剝洋蔥 people

醫生推出手術結束的女性。圖:新京報《剝洋蔥》報道視頻截圖
在陳素文的診室里,問診通常從討論胎心胎芽開始。如果胎兒健康,她會用兩個指尖給孕媽媽比划出胎芽的大小;然而,有時候沒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沒戲了”。
陳素文是北京某三甲醫院計劃生育科的主任醫師。一張桌子、兩張椅子,加上簾後一張做檢查用的床——從計劃生育科室於1978年成立起,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現在;不過,床上躺着的問診者一直在改變。
早此年,檢查床上躺着的幾乎全是要求終止妊娠的女性。如今,就診的病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生育困難的和預約人工流產的。於是,幫助想生的人生好,幫助不想生的人流產,成為了科室服務內容的一體兩面。這些變化讓陳素文感觸良多。隨着婚育年齡的推遲,以及二孩、三孩政策的放開,生育困難群體的佔比越來越大。至於預約流產的人群,她們下決定的原因更加複雜,醫患溝通也變得更頻密。
陳素文在計劃生育科已經待了18年,見證了人口政策變遷下,科室服務人群和內容的變化。她說,生育政策放開了,大家有多生的機會,但這個機會對於每一個人來說並非完全平等的,要看她們有沒有能力來承受這個機會。討論這個能力時,要把她們當成有社會屬性的個體,而不是病人。
遭電擊治療,一位跨性別者決定起訴
出品:澎湃人物

秦皇島市第五醫院。圖:互聯網
8月13日,靈兒(化名)起訴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的線上庭審開庭。靈兒認為,醫院在她不同意的情況下收治她97天,並且進行一系列非必要的治療措施,侵害了她的人身權。
27歲的靈兒,生理性別是男性,性別認同是女性。2022年7月22日,她被父母送去精神病專科醫院。病歷顯示,靈兒的母親告訴醫生,家人在2021年底見到靈兒回家時留着長發、穿女裝、好打扮、化妝,認為其存在精神問題。父母希望她改變觀念,期間因理念不合而經常爭吵。醫院門診基於靈兒有“惡劣心境”,在家屬知情同意之下,將靈兒收入院,並且跟進診斷靈兒具有“焦慮障礙和自我不和諧的性取向”。收治期間,院方對靈兒採取了7次 MECT(改良電休克)治療。
在他人建議下,靈兒將收治她的醫院告上法庭。庭上,靈兒的代理律師之一、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郭睿提出,靈兒沒有暴力傾向、自殺行為,也無危害社會的可能,而且具備完全民事責任能力,應由她自己決定是否住院診療。
不過,靈兒當時的主治醫生王秀奎談及此起“病例”,反問 “(如果靈兒的)爸爸媽媽因為這個自殺了,(靈兒)影不影響社會治安?” 王秀奎是九龍山醫院精神科門診主治醫師,從事精神科臨床工作30餘年。他始終認為,靈兒“患有”性取向障礙。
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早在2018年發布《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ICD-11)》,將性別認同及相關精神狀態問題從精神障礙分類中移除,同時在“性健康相關狀況”章節中增加了“性別不一致”的編碼。同年12月,中國國家衛健委發布通知,次年3月1日起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應當全面使用 ICD-11 中文版進行疾病分類和編碼。
被迫住院和接受治療,只是靈兒“出櫃”後曲折路途的一小段。儘管靈兒針對醫院提起訴訟,面對送她就醫的父母,她不願意與他們對簿公堂。至今,她與父母的關係依然緊張,也難以找到穩定的工作。家庭作為她接觸社會前的第一道屏障,好像憑空消失了,她也還沒做好在社會中穩定生活的準備。另一邊廂,隱匿門後的中老年父母可能也是茫然無措的,往往為了避免受傷而做“鴕鳥”,他們需要有人告訴自己,孩子到底怎麼了、該怎麼辦。眼下跨性別者的家庭能獲得的“再教育”和救濟機會仍然有限,跨性別者獲得家庭認同的路途仍然漫長。
逃離特訓學校後,少年們開始“復仇”
出品:極晝工作室

湖南湘陰一處特訓學校。圖:互聯網
勵志少年軍校、青少年心理培訓學校、戒網癮學校、青少年特訓營⋯⋯這些“學校”的名字不盡相同,但有統一的特徵和模式——主營業務專門針對8歲到18歲有不良行為習慣的“問題青少年”,包括上網成癮、不聽話、早戀、厭學、內向孤僻、不孝順父母等,甚至即便是已經成年的,例如患抑鬱症的文科碩士、沒找到工作的22歲女孩也可能被納入“有問題”的範疇。這些“學校”都實行軍事化、全封閉式管理,有些還會輔以感恩教育、國學教育,聲稱可以通過這些手段去矯正“問題青少年”的行為。
這些“學校”的辦學資質也總是成謎。有當地教育局表示,它們“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學校,而是一家以公司名義註冊的機構(⋯)不屬於教育部門的管理範圍”。與此同時,青少年在這些特訓學校遭遇侵害的事故時有發生。今年8月,江西省安遠縣一名14歲女孩在某訓練營遭負責人侵犯,在警方立案第二日後從6樓墜亡。兩天後,成都新巴蜀特訓營的學生舉報,學校工作人員存在冒充民警、暴力體罰毆打學生的情況。9月4日,河南省鄭州市中牟縣一位家長發文,稱他14歲的女兒在素質教育學校訓練期間,遭遇教官體罰導致昏迷;另一位家長隨後也舉報,他的兒子在該所學校遭遇教官強制猥褻。
這些“學校”摧毀的不只是孩子們的身體——他們都是被父母親手送進去的,那令孩子生出一種強烈的被遺棄感覺。《極晝工作室》的這篇報道,記述了幾名孩子針對一家特訓學校的卧底調查和舉報——當大人不再可靠,甚至成為共謀者,這群受傷害的孩子決定用自己的方式“復仇”。
“研學”降本,降成“跟團游”
出品:北青深一度

學生參加研學活動。圖:互聯網
7月初的一個中午,劉樺坐地鐵途經五道口站時,一群戴着小紅帽、身穿藍色馬甲的孩子在兩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擠進了車廂。這一行有近20人,領頭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隊尾還綴着個年輕女孩;不少孩子熱得滿頭大汗,乾脆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席地而坐。
劉樺湊過去一打聽才得知,這又是一個來北京的研學團,剛剛“打卡”了清華大學,接下來要去奧體中心看鳥巢和水立方。來京兩年,劉樺還沒進過清華校園,好奇地追問校園內的情況。年輕女孩這才坦言:“我們沒進去,就在門口拍了幾張照片。”
收費貴、溢價高、質量差⋯⋯亂象頻生的研學游背後,是研學機構為了“降本”增利而各出奇招。在無門檻限制、無標準考核的情況下,許多研學課程被製作成了給家長的彙報演出。一位前研學導遊向《北青深一度》介紹,譬如乘坐北京西郊線,就會被包裝成打卡“最美西郊線”景點項目,“花很長時間在排隊、坐地鐵、到站拍照上”;譬如北京地鐵一號線也可以說成“中國首條地鐵線路”,說成是體驗歷史項目。據他介紹,市面上正規的地鐵體驗研學需要和地鐵、電車公司合作,安排實地參觀駕駛室、體驗安檢崗位、學習地鐵調度規則等,“但如果只列為研學中的一個體驗小項目,報這些團的家長不懂,也不會細問”。
來自全國各地的研學團不僅“攻佔”公共交通線路,也讓博物館和高校成了黃牛高價倒賣預約名額的重災區。由於票價被搞亂,遊學團臨時改變收費標準也是常事。有家長告訴《北青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為三年級的兒子報名了暑期研學夏令營,7月開營前卻被機構告知要加收500元。負責人告訴她,加價的原因是幾個原定的景點預約爆滿,機構也需要從“黃牛”手中高價收票。
一位從業多年的機構負責人稱,本來研學游安排得怎麼樣、課程設計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現在,孩子們的研學體驗,依然取決於成年人的良心”。
“沒苦硬吃”的中式父母,讓年輕人有多無奈
出品:穀雨數據-騰訊新聞

圖:穀雨數據-騰訊新聞
最近,老一輩“沒苦硬吃”的話題在各大平台引發年輕人的共鳴,話題登上熱搜,還有博主把網友的吐槽編成歌詞:有福我不享,沒苦我硬吃。沒病我找病,有病我硬扛。節約三五塊,多花三五百⋯⋯
該視頻在抖音有超過10萬條評論,在 B 站有超過250萬播放。就這個有趣的題目,騰訊新聞的“穀雨數據”整理了網絡評論、論文、研究數據等,檢視年輕人眼中老一輩的“硬吃苦”方式,兩代人之間的分歧和理解,並且分析老一輩“沒苦硬吃”的原因。
在年輕一代的集體吐槽中,可以看到老一輩五花八門的“硬吃苦”方式——為了省10塊錢打車費,延誤了飛機,花了3500改簽;藥物快過期了怕扔了浪費,最後全吃了,藥物中毒住院;小錢節省,大錢卻花得隨意,迷信電視廣告里幾百上千的保健品⋯⋯
不過,綜觀年輕一代的吐槽,也可以看到兩代人之間的觀念鴻溝。在5126條抖音評論中,有31.8%年輕人對老一輩“沒苦硬吃”感到崩潰煩躁,但也有近三成年輕人表態願意換位思考、理解,或者願意積極勸說,好好溝通。
從網絡評論中,可以聽見年輕人的聲音,卻較難了解老一輩的真實想法。老年人“沒苦硬吃”的原因,可以從相關論文探個究竟。有論文分析出生年代對老年人消費習慣的影響,認為饑荒、貧困等成長經歷整體上塑造了老年人保守、實用、節儉等習慣。此外,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顯示,60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消費結構中,食品和醫療支出兩項明顯超出全體居民,其中醫療支出幾乎是全體居民的兩倍。換句話說,老年人“沒苦硬吃”的背後,可能還有對未來的憂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