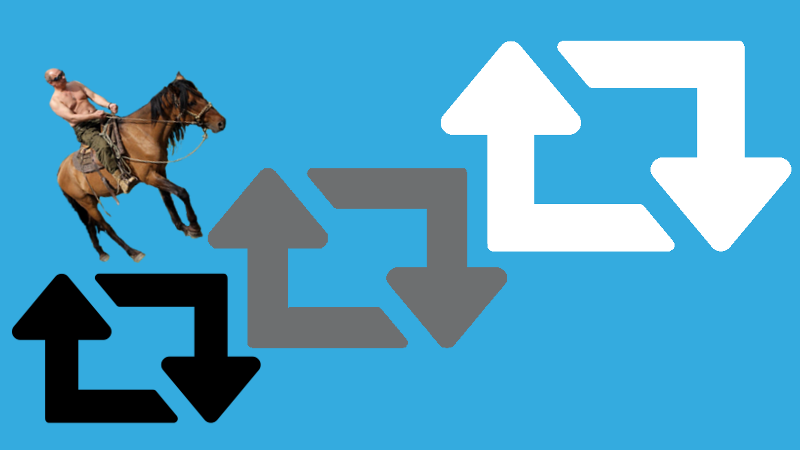1.
“你知道這次的大會,邀請了一個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下毒的俄羅斯女記者嗎?”
剛見面,朋友 J 就問我。我搖頭,只覺得這個會場一下子變得不安起來。
這是全球大流行之後的第一場全球調查報道大會(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nference)。據主辦方 GIJN 稱,這是歷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球調查報道大會,來自全球各地的新聞媒體人有兩千多人。在這個九月份已凄風苦雨的瑞典城市哥德堡,我們將有機會參與來自全球新聞從業人士的講座和分享。
會議組織的井井有條,一同參加會議的記者們,都震驚於主辦方的後勤能力——連續五天,每天都有十幾場講座和分享,如大學選修課般同時進行,參會者只能在眾多吸引人的“課程”中,參與一部分,割捨一部分。
只是當 J 提到被下毒的俄羅斯記者後,我們在會場的大廳,邊啃着主辦方準備的麵包,邊突然驚覺,這裡會不會有俄國特勤局的人來。“如果把這兩千多個人都消滅了,全世界的獨裁者應該會睡個好覺。”另一個人笑着說。
整個大會幾天,我們一直開這樣的“地獄玩笑”,有時候是我們在台下開,有時候是講者在台上開,如同一種另類的集體心理診療。
我說自己報名了第二天的“俄羅斯調查資源”(Resources for Investigating Russia)。
說來巧,來大會之前,我和 J 兩人身處不同的歐洲國家,卻幾乎同時讀了《紐約客》去年的著名報道《流亡海外的俄羅斯記者如何報道俄烏戰爭》(How Russian Journalists in Exile Are Covering the War in Ukraine),並且都在社交媒體發表了一番相似的感慨。
那篇報道講述了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的多家獨立媒體被封禁,並且重新在歐盟境內——主要是在荷蘭或拉脫維亞重新安營紮寨,繼續報道俄羅斯的故事。Meduza、TV Rain 和《新報》(Novaya Gazeta)都在報道中被提及,但這位被 FSB 投毒的女記者並沒有在報道中提及。
2.
第二天中午,“俄羅斯調查資源”的分享如期舉行,我懷着莫名忐忑進入會場,找位置坐下,好奇會是怎樣的“危險”人物到來。我稍感意外,會議並未任何嚴格限制,只需出示記者的與會名牌即可。攝影機在後方拍攝,看上去也會公開報道,毫不擔心俄國干涉。

iStories 的創辦人羅曼·阿寧(Roman Anin)在 GIJC23 發言。圖:Leonardo Peralta for GIJN
主持人和兩位俄羅斯記者一起上台,他們的照片隨即投影到幕布之上。幕布里,男記者羅曼·阿寧(Roman Anin)托腮望向鏡頭,面孔青春而消瘦,如音樂專輯封面上叛逆沉靜的酷男孩。他是獨立調查媒體 iStories 的創始人和主編。這家媒體擅長開源調查(open-source intelligence),屬於“技術流”的獨立媒體。當然,由於它們常年報道俄羅斯政治腐敗,目前也“移居”到了拉脫維亞。
現實中的羅曼並不像那張照片,他看上去滄桑和強壯許多,多數時候不苟言笑,但在回答主持人問題時,總是口若懸河,也常開各種“地獄玩笑”。在面對主持人提問,如何平衡新聞倫理和技術手段的運用時,他首先說了句“我他爹的不在乎”(I don’t give a shit),接着才解釋說,“我們首先得是一個人,得有人性,再是新聞倫理,烏克蘭人每天都在死亡。”
另一個人,就是那個被下毒的女記者,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照片里她一臉溫柔笑意,眼神明亮。她同樣比照片看上去滄桑和憔悴,說話總輕言細語,時不時自嘲自己被下毒這件事,並且她用的詞總是“據說被下毒”(allegedly poisoned)——這讓我覺得有些滑稽。一個遭遇如此暴行的新聞記者,在面對自己被下毒這件事時,仍然在渴望保持某種客觀,這未免對自己過於殘酷。
是怎麼樣的組織,會想去殺死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鑒於台上的兩位記者都已經離開俄羅斯,而俄國卻是他們所從事報道的主要對象。因此,主持人一直在好奇,“現在你們已經離開俄羅斯了,你怎麼從俄羅斯內部去搜集信息、進行調查?”
儘管“據說被下毒”的伊蓮娜更讓我好奇,但眼下,我應該先記錄一下羅曼·阿寧的回答。他回答得更多且帶着更多希望,“戰爭開始前與之後,我們的工作方法並沒有明顯差別,甚至我們的方法,變得更重要了。”
他大意是說,在 iStories,他們同樣會採取部分傳統的方法,也就是採訪。另外,他們根據開源信息進行網絡調查。另外,他們“利用俄羅斯的數據黑市,去購買那些黑客獲取的資料。” 他們同樣將編程和人工智能融入新聞調查,“在十年前,我們只能一行一行地去讀這些文件,現在我們有了 Python,可以用代碼來分析這些材料。”
羅曼提醒在場的諸多記者,“壞人也使用社交媒體”。他們通過照片上的人像,用人工智能去識別這是否是那個他們要找的人,因為有時候,人類識別照片的能力反而不如機器。他舉了一個尋找俄羅斯士兵的例子,iStories 的記者在新聞媒體上發現了他們的照片,然後在社交媒體上找到了他們,一個個地打電話過去,“其中一個人,甚至對我們懺悔自己殺害了村民。”
比起伊蓮娜,羅曼顯然更樂觀一點,因為許多全球互聯網熱門應用,在俄羅斯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有一樣東西對我們的工作至關重要,那就是互聯網。因此,整個社會應該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比如大科技公司完全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們目前沒有這麼做。我們聯繫過他們,他們根本不幫我們。在 Google 上,如果有 10 個俄羅斯人用它搜索(俄語)新聞,10 個人看到的都是來自俄羅斯的宣傳。當我們試圖聯繫那些科技大佬們,我們嘗試在俄羅斯國內傳播真相,但他們什麼也不做。類似於谷歌這樣的公司,其實應該做得更多。”
“如果有一天,俄羅斯變得越來越像其他一些國家,完全不能使用這些服務,我們作為調查記者能做的就不多了。”羅曼說。
羅曼在台上講,我在台下查閱他的資料。

羅曼·阿寧(Roman Anin)在 iStories 的個人介紹頁。圖:iStories 網站截圖
他和他創辦的媒體,比伊蓮娜更早被迫離開俄羅斯。和伊蓮娜一樣,他也曾是俄羅斯著名的媒體《新報》(Novaya Gazeta)的記者,1986 年出生,比我大不了多少。在 iStories 的網站上,他的第一句自我介紹就讓人難以忘懷——“我實際上一直想當一名足球員”(I actually always dreamed of becoming a footballer)。他進入莫斯科國立大學新聞學院學習,加入《新報》,渴望改變俄羅斯。與此同時,普京在 2012 年通過了《外國代理人法》(Russian foreign agent law),國際 NGO 被集體驅逐。他抱着雄心做俄羅斯國內政治、社會、腐敗調查,整體新聞環境卻在急劇惡化,很多人轉行去大銀行或大公司做公關。隨後他和同事一起創立 iStories,再然後,這家媒體被貼上“外國外國代理人”標籤,很快,他本人也被貼上“外國代理人”標籤,他因此擁有了獨一份的“雙重外國代理人”身份。
當時是 2021 年,他正結束在拉脫維亞的度假,接到了許多採訪來電,問他對自己的身份有何感想。俄國本國媒體比他先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但很快他就意識到,他和他創辦的媒體都不再能回國了。
俄烏戰爭爆發後,他仍在繼續工作。2022 年 3 月,他接受了 Vice 的一段專訪,一年前他的回答並不像在這次大會上那麼樂觀:“作為一名記者,如果不能在你所報道的國家生活,那太荒謬了。但就我而言,我別無選擇。”
在流亡中報道,是他現在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在那篇採訪中談過“退意”:“任何報道,都不值得記者去送命。因此,如果這種威脅對我或我的同事來說成為現實,我會離開(新聞業)。問題是,我們都是樂觀主義者,認為即使是最危險的報道也不會成為殺死我們的理由。”
“十年前,我會告訴你,我想成為一名記者,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現在,我認為俄羅斯記者更像是歷史學家。我們的工作是為後代保存歷史。這樣,20 年後的年輕人就會知道,納瓦利內(Navalny)並沒有像俄羅斯主流媒體所說的那樣毒死自己;這樣,年輕人就會知道,誰才是真正在烏克蘭戰鬥的人。”
而眼下他身邊坐着的,就是自己的前同事,差點為了報道而送命的伊蓮娜。
3.
和羅曼不同,伊蓮娜面對主持人提問的回答是更為否定的。我想這部分是因為對她來說,移居外國仍然是新鮮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並且她還在流亡德國期間,在無形中身中劇毒。
“這對我來說真的很難,因為我是一個實地調查的記者(a field reporter)。”伊蓮娜說。

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在 GIJC23 會場。圖: Leonardo Peralta for GIJN
俄烏戰爭一開始時,她還是新報記者,被主編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2021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派去烏克蘭做現場報道,去那些一開始被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城市。她穿越重重邊界,向俄羅斯發回前方的戰地報道。儘管她生於 1987 年,但早在這以前,她已經做過近17年記者,是一名新聞老兵,親歷過《新報》同事的死亡,也組織過前同事的葬禮。但這一次前往戰場的實地報道,才真正成為她大禍臨頭的根源。
她在《新報》上發表的報道,後來紛紛被俄羅斯司法部門勒令刪掉,連《新報》本身也在俄羅斯被取締,被迫“移居”到了拉脫維亞。現在你再按圖索驥,去查找伊蓮娜在新報的一些報道鏈接,只會顯示 404。那被俄羅斯當局勒令新報刪除——據伊蓮娜所說,她最崩潰的一刻,不是在她被投毒時,也不是在得知自己無法回國時,而是當她發現自己的報道統統被當局勒令刪除時。
好在,我後來在 n+1 雜誌上上找到她的報道英文版。那是四篇如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 《二手時間》一般的報道:“逃離烏克蘭-沿着難民之路”,“駐防敖德薩—我不能放棄自己的城市”,“放過我們—在邁科拉夫”,“在赫爾松—被占之城”。
除了通過她的眼睛,讀者能看到現場發生什麼之外,伊蓮娜還成段成段地使用直接引語來講述故事,讓受訪者直接敘述自己的遭遇,也因此立刻讓人想起阿列克謝耶維奇採訪“後蘇聯居民”的諸多非虛構作品。
這些報道讓我明白為何她說現在的一切變得更艱難,為何她說自己是一個需要實地採訪的記者。以最後一篇《在赫爾松》為例,她在這個戰場前線只待了三天,卻至少採訪和記錄下了這些人:前市長、軍事指揮官、戰士、當地記者、當地人道援助者、主任醫師、商店經營者、法醫辦公室、俄羅斯佔領的地區委員會俄國守衛士兵、當地需要食物和醫療的普通居民、尋找失蹤孩子的父母、被綁架的人、烏克蘭抗議者們……
她在 2022 年 3 月 18 日到 21 日採訪了這些人,離開赫爾松,寫作,在3月26日,發表了這篇被佔領區的顯微鏡一般的報道。作為一個前同行,我知道這意味着何等的體力、勇氣、心理和智力勞動。
伊蓮娜沒有隱瞞她目前身處德國的困境,她說自己在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去進行書寫。
“我們作為調查記者,有時候發回大量報道,卻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因此,我覺得我有必要找到一種新方式來向我的人民、我的國家發聲,因為他們受了太多俄羅斯宣傳的影響。我懷疑傳統形式的新聞報道是否能像在(俄羅斯)入侵以前那樣,還能發揮作用。因此,我決定重新審視自己過去17年來的工作,一種全新的、誠實的態度,去看待自己和自己作為記者的經歷。成果就是一本書,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全新的形式。”
“之後,我將會繼續進行我的實地報道,因為俄羅斯現在影響着全世界很多國家。而我現在所做的,基本上是搜集從俄羅斯來的信息,還在俄羅斯的俄羅斯人,仍然有相當多希望能夠記錄那些真實……但後來……我又據稱中毒了,現在我還在恢復中。”
伊蓮娜談話時仍顯虛弱,和她談論的“猛烈”議題形成劇烈反差。
她謙遜且有所保留,並未詳細說明為何她不再回到俄羅斯,沒有談論自己的家人和愛人,也並未說明那一場中毒事件的細節。她只是在艱難地回答主持人這個殘酷的問題——作為一個書寫自己國家的人,如果我回不去了,我還能做什麼?
我對俄語一無所知,在這場戰爭以前,也並未跟進那麼多俄羅斯獨立媒體,因此對她的經歷更為好奇:她為什麼回不去了?她是怎麼中毒的?她寫了一本怎樣的書?
4.
那場分享結束後不久,她在《衛報》發表了自述,《“你可能被下毒了”:一名獨立俄羅斯記者如何成為眾矢之的?》(‘You may have been poisoned’: how an independent Russian journalist became a target)。
“很長時間以來我都不想寫這篇文章,我感到噁心、恐懼和羞愧。”開篇她說。

伊蓮娜在《衛報》上她發表的自述《“你可能被下毒了”:一名獨立俄羅斯記者如何成為眾矢之的?》。圖:《衛報》網站截圖
這部分解釋了為何她在分享中,總是不願過多談論她被下毒的事情。在她的書寫中,她說自己在俄羅斯時,鑒於自己的5個同事都死於非命,她總是小心行事,遵照職業手冊的一切安全措施。但當她來到德國後,卻覺得“這裡是歐洲,應該安全了”。
只在中毒兩個月的生不如死後,醫生才排除了中毒以外的所有可能,並通知了德國警方介入調查。她與德國探員談話時,德國探員用一種責備的語氣說,“我不明白你為什麼兩個月後才報告給我們……你們來到這裡,彷彿自己在度假,這裡是天堂一般。我們這裡發生過政治謀殺,俄羅斯特勤局在德國非常活躍。”
在中毒以前,她不斷從烏克蘭戰爭前線發回的報道,已讓她成為眾矢之的。在發回以上四篇報道後,她還決定繼續前往新的戰場——馬里烏波爾。那以前,她的同事突然來電警告她,俄羅斯國家近衛軍(National Guard of Russia)的車臣分隊決定殺了她,這已經得到批准,並且有電話錄音為證。烏克蘭方面的聯絡對象也提醒她,俄羅斯正在組織暗殺一名新報的女記者。再過一小時,總編輯穆拉托夫打給她,敦促她必須馬上離開烏克蘭。
為了不牽連載她去馬里烏波爾的烏克蘭受訪者,她不得不離開烏克蘭現場。她決定回俄羅斯。但那已成為不可能。
總編輯穆拉托夫對她說,“我知道你想回家,但你不能回俄羅斯。他們會殺了你。”
伊蓮娜掛了電話,在街頭尖叫——但她並未寫這一刻,她在哪裡尖叫。
根據後文,我猜測她那一刻在柏林的街頭大聲喊叫。一個寫了烏克蘭戰地系列報道、受到直接暗殺威脅、渾身因長久沒洗澡而長滿虱子、得了腮腺炎和強烈創傷應激後障礙的,勇猛的女性記者,在那一刻徹底崩潰了。
她中毒的經歷更為驚悚,一切發生於無形,且是在後來與德國聯邦探員的不斷追溯過程中,她才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回到那些列車上、飯店裡、慕尼黑的咖啡廳和柏林地鐵站的細節里。她一直不肯相信自己被下毒了,儘管她已全身浮腫,面目全非,不可入眠也無法清醒。她本已加入新的媒體“美杜莎”(Meduza),正在籌備去伊朗現場的簽證,但她不得不放棄這個工作。她也無法再寫那本書了。那是生不如死的兩個月。但在醫生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後,她只能相信這件事。
醫生認為,她身中的,是一種“氯有機化合物毒藥”(chloro organic compound poison)。
近一年後,來到 GIJC 的會場時,她的臉、手、腿不再腫脹,不再疼痛到無法觸摸,但她不得不離開她的新東家“美杜莎”(Meduza),她在文章最後寫道,“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希望活下去。”
“我知道記者會被謀殺,但我不願相信他們會殺了我。反感、羞恥和疲憊,讓我去遠離這種想法。想到有人想要我的命,我就覺得噁心。我羞於啟齒。即使是對親人也是如此,更不用說對警察了。我知道自己有多精疲力竭,體力所剩無幾,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逃亡了。”
但她最終還是完成了那本書。返回德國後,我在等待伊蓮娜的新書出版。我想知道伊蓮娜所談的一種全新的書寫形式是什麼。

《我深愛的俄國:發自迷失之國的報道》(I Love Russia: Reporting from A Lost Country)封面
2024 年年初,我終於讀到了這本書——《我深愛的俄國:發自迷失之國的報道》(I Love Russia: Reporting from A Lost Country)。我想這本書的內容、寫法與結構,對許多記者來說,都應該是一本啟發之書。這除了是一本俄羅斯在後蘇聯時代的當代社會和政治史變遷以外,也是伊蓮娜的個人史、家庭史;她作為同志女性的愛欲史;她和羅曼·阿寧這一代俄國記者一樣、曾希望通過新聞記者的努力改變俄羅斯、而最終失落離去的消亡史。
在結束對她的探索前,我想引用一段該書第九章的故事,“我的第一場戰爭(媽媽和克里米亞)”( My First War (Mama and Crimea) )。那是發生在家庭里的內戰,屬於兩代人的失落戰爭。
媽媽懷念蘇聯,當烏克蘭發生邁丹革命時,媽媽覺得法西斯又來了。當克里米亞“公投”而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後,她歡欣鼓舞,終於美麗的克里米亞回到了“我們的懷抱”。
她頻繁打電話給女兒。兩人每一次都爆發激烈的爭吵。在任何公共事務上,她們都處於南北兩極。那些對話極為精彩、真實和令人疼痛。更換到另一個國家的語境,這一切也對我來說太過熟悉。
我不知道伊蓮娜在德國書寫這一章時的心情。她將再也沒法回到俄羅斯,回到她的家鄉去見到自己的母親。
5.
“在場的有多少人是流亡記者的?”
一個足以容納兩、三百人的大場下,有十來只手舉了起來。
“有多少人覺得自己是在流亡邊緣的?”
我和 J 先是面面相覷,彼此覺得自己符合這種“on the verge of becoming an exile”的定義,默默舉起手來。同時,會場上許多的手都舉了起來,提問的講者隨即笑道,“看來各位都是。”
然後現場爆發出一陣大笑。看,這又是一個來自講者的“地獄笑話”。
此刻我們在第三天的其中一場會議,“流亡媒體:生存策略”(Exiled Media: Survival Strategies)。這大會期間,我還參加了烏克蘭記者的戰爭犯罪調查分享,也參加了人口販運跨境報道的分享,還有自由撰稿人如何報題與生存的分享……但我最期待的,除卻“俄羅斯調查資源”以外,便是這一場。

“流亡媒體:生存策略”(Exiled Media: Survival Strategies)的三位講者。圖:Smaranda Tolosano for GIJN
因為從題目來看,它並不僅是一個“各國流亡媒體現狀”的一般講座,它準備告訴你一件事:如何在海外,作為個人和作為媒體機構,同時生存下去?
向觀眾提問的是這場會議的講者之一,她名叫波利娜·瑪喬德(Polina Machold),俄羅斯獨立媒體 Proekt 的出版人。和她同場分享的,還有來自委內瑞拉流亡媒體 ARmandoinfo 的總監約瑟夫·波利祖克(Joseph Poliszuk),和孟加拉國流亡媒體 Netra News 的創始人塔斯尼姆·卡哈利(Tasneem Khalil)。
儘管另外兩位的分享也讓我大開眼界,從流亡媒體的報道實踐中,我更了解到兩個國家的新聞、政治和社會生態。但目前,最能引起我興趣的,永遠是來自俄羅斯或烏克蘭的記者。
我仍習慣於觀察和記錄講者的外貌特徵,這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外表評判,而是當一大群來自世界各地的危險記者相聚於此時,通過外表,你已能看到彼此的許多創傷。羅曼·阿寧顯得憤怒和激烈,有時甚至透露出難以壓抑的玩世不恭;伊蓮娜則寡言少語、疲憊而感傷,像剛從死亡深淵中爬出來;而波利娜,她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個 TED 演講者。

俄羅斯獨立媒體 Proekt 的出版人波利娜·瑪喬德(Polina Machold)。圖:Smaranda Tolosano for GIJN
她剃掉了兩側的頭髮,留了一頭基利安·墨菲(Cillian Murphy)在影視劇《浴血黑幫》(Peaky Blinders)里的髮型,簡潔幹練、黑色西裝、白色休閑褲、總保持禮貌而冷靜的微笑;再加上她的條分縷析,足以讓所有人感受到她的思慮周全和強悍自信。
Proekt 於 2018 年在俄羅斯創辦,她們專攻俄羅斯政治腐敗的調查報道。在 2021 年 7 月 15日以前,該媒體在俄羅斯算是合法運營,是碩果僅存的幾家本國獨立調查媒體。波利娜在講她們在俄羅斯境內做的題目時,那些選題在我聽來不可思議,原來俄羅斯曾經還有這樣的“自由”?比如,她們對車臣領導人拉姆贊·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家族財富的調查、俄羅斯當局操縱統計數據、以及普京的情人、財富和他隱藏的孩子。
而在 2021 年 6 月底,在 Proekt 宣布即將公布對內政部長弗拉基米爾·科洛科爾采夫(Vladimir Kolokoltsev)的腐敗調查後不久,情況急轉直下。
“在我們發布這份調查報告之前的黎明,警察突襲了我們三位記者的房子。這是一個明確信號,表明是時候了。我們需要離開俄羅斯了。在他們被釋放後,我們整個團隊,進行了一次激烈的大討論,討論我們該怎麼辦。當然,我們早有緊急預案,甚至制定過按小時計算的、我們能想到的各種安全措施。記者們也都提前準備好了護照、申根簽證……”
“但問題就在於,什麼才是那一個‘最後的信號’?”
她們的預感是對的,兩周以後的 7 月 15 日,俄羅斯總檢察長辦公室將 Proekt 列為俄國法律上的“不受歡迎組織”(Undesirable organization)。在俄國法律中,“不受歡迎組織”比“外國代理人”更為嚴重。
2021 年《俄羅斯刑法典》修訂後,刑法規定多次與“不受歡迎組織”合作的個人,可能會面臨長達4年的監禁;而被認定犯有 “組織此類組織活動罪”(organizing the activities)的人可能會被判處長達6年的監禁。而 Proekt 是俄羅斯第一家被貼上“不受歡迎組織”標籤的媒體。

Proekt 是俄羅斯第一家被貼上“不受歡迎組織”標籤的媒體。圖:網站截圖
“這一消息宣布後,所有俄羅斯媒體,都立即刪除了我們網站的所有鏈接。人們也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刪除我們的鏈接。我們因此失去了所有的傳播渠道。這可以理解,但也讓我們失望。因為很明顯,我們只是第一個靶子。我們成功地激怒了普京,但我們不會是唯一一個。看看過去兩年戰爭以後吧,情況要糟糕得多了(更多的“不受歡迎組織”出現了)。”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她向現場提問。
6.
她一邊展示原有團隊成員在解散前的最後一張合影,一邊講述那以後的“生存策略”。
首先需要的兩件事情:錢和人脈。沒有錢和人脈,作為組織和個人都會迷失方向,寸步難行。
其次,她們立即關掉在俄國國內無法再合法運營的法律實體。俄國從此不再存在這個“不受歡迎組織”。
接着,切斷所有國內的眾籌和捐款,因為在俄羅斯,所有向不受歡迎組織捐款的個人,都可能受到刑事起訴。
然後,拿出早有預備的應急基金——這是 Proekt 成立以來就一直儲備的一筆錢。它將用來幫那些願意離開的記者,在新的國度安頓下來。
同時進行的,是向海外的媒體夥伴尋求幫助,這是重要的資源、人脈和能力。沒有這些幫助,Proekt 將無法實現“搬家”,更無法在一個全新國家,迅速設立一個新辦公室。
這是這家媒體選擇流亡的前兩個月發生的事情。
不是所有團隊成員都願意相信這是“最後信號”。更多記者也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國家。波利娜追憶了那些對話。
“如果你想繼續和我們一起工作,那就不要回來。”
“如果你不想離開這個國家,我們就立刻終止合同。”
“在這裡,我不能保證你的安全。我的責任和良心,都不想讓你因為我們的工作而進監獄。”
出乎她的意料,許多人選擇離開新聞業,留在俄羅斯。Proekt 本來是一個 20 人左右的團隊。而這一次實施的緊急措施,導致的直接結果,是一半成員就此離開。而對於那些願意繼續去到新國家展開工作的記者,波利娜將她們一個一個送到機場,目送她們上飛機,和她們說再見。
她自己最後一個離開俄羅斯。
“我想現在所有人都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但很多人仍不關心這些事情的重要性。(記者們)有金錢問題、住房問題、辦公室問題……這很重要,因為你是會崩潰的。想想看,在一天之內,從自己的家園,搬到另一片土地,在一個整體上充滿敵意的新聞環境中,這真的極盡艱難。”
“要幫助找到能和她們說話的人,你自己也要和她們說話,注意每個人的心理健康,這一點至關重要。如果你不能儘早設立辦公室(讓大家見面),那最好的辦法,是讓大家先能互相交流起來,你可以把她們安排到一起居住,定期一起吃個早餐。”
當這一切完成後,剩餘的團隊要保證,能夠繼續工作。這是她們離開的目的,是她們要保存和奪回的東西。提前思考,開展業務,努力如常。“因為人力減少,加上諸多動蕩,可以減少調查和新聞,但不能停下來,什麼都不做。”
最後,波利娜給了在場的新聞人一個提示,不要忘記在安全的支付手段下,如“加密貨幣”的手段之下,向你的觀眾和讀者請求捐款和訂閱。
“在俄羅斯,當有人被封殺、或被貼上外國代理人、或“不受歡迎組織”的標籤、或被關進監獄、或遭到警方突襲,人們會用金錢來回應。他們不能大聲說話,但他們會用金錢來回應,這讓你看到你得到了多少支持。這真的很有影響力。它為你提供了精神上和經濟上的支持,在危機時刻,這份支持非常寶貴。”
我被波利娜的演講吸引。越聽波利娜講話,越能感到她帶有某種強大的氣場和說服力——她不是那種只有“大局觀”的人。反而,通過她的講述,你開始理解,她面對着所有記者們要面對的問題。她反覆強調金錢的重要性,強調每個人的心理健康,強調要有緊急預案、儲備資金,強調異國搬遷的媒體組織要對記者展開的多重支持。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這樣的前輩極為罕有。當我面對所有的經濟和安全問題時,總是在獨自應對。
而波利娜一直在強調金錢、關係、心理健康對於移居海外做記者的首要性。在所有這些以後,才是保持工作,保持勇敢,因為那是你離開的目的,也因為“你不會再一次失去你的國家”。也因為“一旦你選擇遷徙,你可能就會永遠遷徙”。
Proekt 團隊就是如此。她們最初是搬到了格魯吉亞,但由於俄羅斯的政治影響,團隊的一些記者在離開格魯吉亞開會或出差以後,便被格魯吉亞當局拒絕再次入境了。波利娜和團隊不得不再一次遷徙,遷徙到歐盟境內。她們沒有停止工作,在俄烏戰爭爆發以後,再一次做出了震撼的調查。
“戰爭以後,我們有了真正有影響力的故事。我們對贊助俄羅斯侵略的俄羅斯寡頭進行了調查,其中一些人最終受到了國際制裁。我想,並不是只有我們找到了這些證據,但我們增加了這些案件的線索和文件,這一切都會出現在國際法庭的證據里。如果你有足夠的耐心和動力,你終究看到結果的,或者……你的孩子會看到。”
隨後的問答環節,於是變得更像是一場記者的集體心理治療。有來自布隆迪、流亡在肯尼亞的記者分享自己流亡和政變的經歷,有來自保加利亞的記者提問……最後,連我這個前記者,也忍不住問了三個問題:關於記者家人的安全問題;關於媒體流亡以後的目標讀者是誰的問題;關於媒體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是準備做永遠的流亡媒體嗎?還是有一天,你和你的媒體,都會回到你的國家?
對前兩個問題,她有非常務實的技術型回答,儘管那些回答並不輕鬆。但在這場危險者聚會的末尾,我只想引用她對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
我們都知道,在目前的情況下, 我們不能回去。
我不知道如何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是的,很多人都會想,我想回家,我可能會在五年內回家吧……但設定一個固定的回家時間,這是一個心理的陷阱。
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打算回去,因為我想在這裡,建立自己的生活,並變得資源豐富、足智多謀。
我將繼續為我們的觀眾、讀者和全世界的俄羅斯人工作。
我們無法預測未來,我們只能做我們的工作。
作者鄒思聰,現居德國,自由作者,曾為職業記者,2023年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獎學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