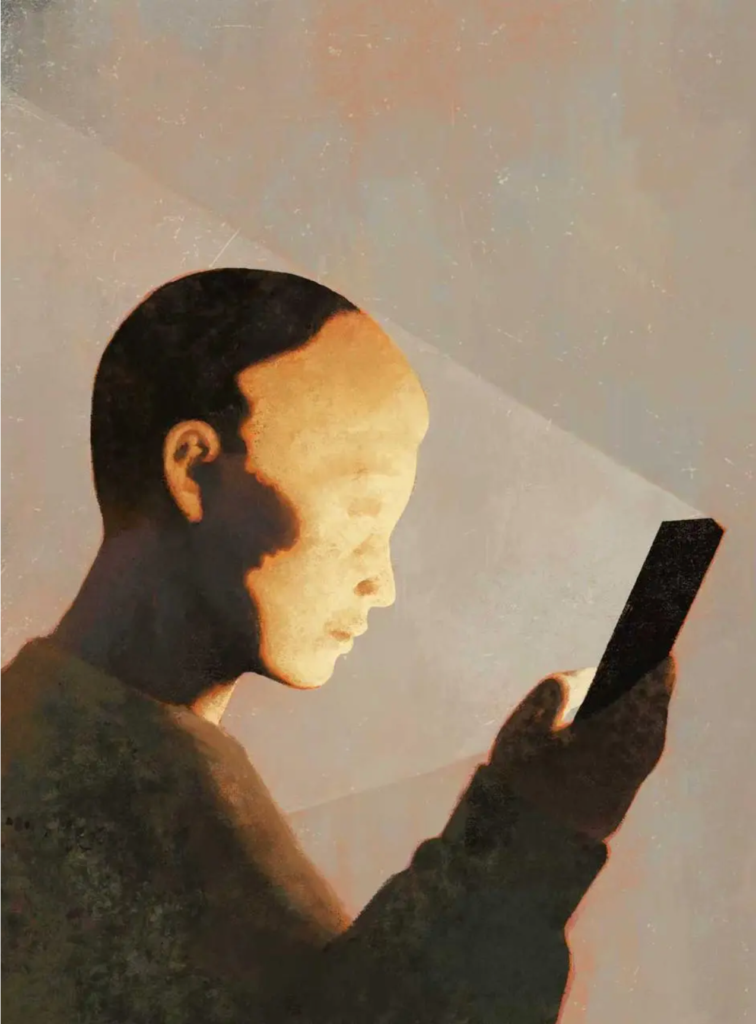《她的名字是》(Hennes namn var)節目封面
過去三年,因為新冠疫情,我的生活和工作變得封閉。2022年在反覆封控下,我沒有出過一次差,絕大多數報道都基於電話採訪,可以正常操作、發表的選題也越來越少。我感到自己的視野、對世界的理解在收縮,也感到了整個行業的消沉——同行們普遍倦怠,認為這份工作在我們的社會中已失去活力,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
於是我申請參加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希望能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聽聽他們都面臨哪些困難,如何度過,更重要的是找到解法,哪怕只是一些微小的提示。我想,活力和信心最終還是取決於一個問題:新聞還有哪些新的可能性?
創新的呈現方式
我受到的第一個啟發來自一場名為《如何以創新方式呈現調查報道》(Presenting Investigations In Innovative Ways)的分享,兩位《哥德堡郵報》(Göteborgs-Posten)記者介紹了他們的一個包括播客和紀錄片在內的多媒體項目——《她的名字是》(Hennes namn var),它講述的是一個19歲的女孩被男友用鎚子砸死之後拋屍湖裡的故事。
親密關係中的暴力,這是一個常常被報道的主題,但他們說,你還可以用新的方式來呈現。
新方法的核心在於“視角”,首先是受害者視角。在案件發生後,人們普遍用“那個被扔進湖裡的女孩”指代受害者,這意味着女孩不但被奪去了生命,並且會永遠被以此記住、命名。記者們由此想到,要建立一種新的敘事,從受害者出發,“視角首先是她,她不是她死去的方式——她有朋友,有夢想,有悲傷”。
以受害者作為故事主角並不新鮮,但當記者們播放紀錄片時,我才明白什麼是他們口中的“視角”——鏡頭是以第一人稱視角切入、推進的,觀眾跟隨故事,像跟隨女孩生前一樣,和她的朋友一起去學校、走在路上、一步步滑向悲劇。直到她的媽媽發現她被殺,報警,但沒得到任何幫助。這種敘事方式的特別之處在於,你不僅可以了解這個故事,還可以經歷,你會很深切地體驗到她們如何孤立無援,沒能及時得到救助。
記者沒有沉溺在個人敘事中而忽視公共議題。整個社會系統為什麼沒能挽救受害者?在這個系列紀錄片中,每一集都有一個醫療、警察、社會服務機構犯錯的案例——他們原本能阻止暴行,但沒做到。
但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片子仍然用到了創新的視角:在最後一集,記者出鏡了,她原本的身份是記者,但最終揭開她的身份是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朋友——她的女友也死於親密關係中的暴力。
片子結尾處,視角又切換到了一位受害女性的母親——她有很多問題想要質問當局。影片最後的影像是她坐在那兒,手裡纏着女兒的頭髮,提出這些問題。片子放完,分享的記者說,過去作為調查記者,總是我們在追問公權力,但最後我們決定讓受到傷害的人自己來說話。
這整個操作案例給了我很大啟發,因為這樣的選題並不罕見。特別是在我們的社會中,幾乎每時每刻都有類似的事發生。我們往往覺得它們並不新鮮,背後的問題也不新鮮。但瑞典記者在面對“舊問題”的質疑時會說:這個問題至今沒有被解決,那麼它就是當下的問題,而不只屬於過去。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新的、更有力的敘事方式呈現這些議題,同時可能也需要去探索新媒介——《她的名字是》的呈現形式是視頻和播客。它的確比文字更具備“讓人聽到當事人開口講話”的力量。

播客《強迫婚姻》(Dipaksa Kawin)的封面
在另一場講座中,印度尼西亞的廣播新聞機構 KBR 主編 Citra Prastuti 也講述了類似的敘事方法——從受害者角度出發的講述。2022年,KBR 推出了播客《強迫婚姻》(Dipaksa Kawin),記者們採訪了很多印尼童婚的倖存者,從中選擇角色,同樣是以受害女性的視角講述,推動故事發展。除此之外,Prastuti 還介紹了一個創新的工作方式:圍讀。把文案大聲讀給同事們聽,通過他們的即時反饋來打磨故事。
新聞專業主義的意義
讓我收穫了最多“乾貨”的一場講座主題是:如何做好調查報道的編輯(Investigative Editing: Best Practices)。一是不久前,我剛開始嘗試編輯的角色,實操中遇到不少障礙和困惑;二是這樣看似“基礎”的討論,讓我重溫了日常工作環境中已漸漸淡化的新聞專業主義。
OCCRP(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道項目)的創始人兼編輯 Drew Sullivan 強調了制定採訪計劃的重要性。他首先講到了一個我們工作中的確經常遇到的情況:記者到處做採訪但拿不到關鍵信息,花費數月還寫不出報道,最後機構不得不放棄這個選題。他分享說,這實際上是編輯的失職,一個好的編輯應該確保記者先找到了支撐故事的核心信息,之後才可以做其他事。
第二個重點是關於主題。要不斷提醒記者稿子的主題。關鍵不在於編輯要知道這些答案,而是因為不斷重複能幫助記者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墨西哥媒體 Quinto Elemento Lab 的編輯 Alejandra Xanic 則說,由於報道的主題隨採訪會不斷變化,她會讓記者寫下來,像便利貼一樣粘在辦公桌上,每次在桌前坐下就能想到它。和記者溝通時她還會寫筆記,記錄本周記者得到了哪些信息、出現哪些問題、解決了哪些問題。筆記應該是一個可以和記者一起編輯的文檔,記錄下對話中提到的最重要的場景、細節、人物,以免記者在海量素材中,最終遺漏掉這些珍珠。
美聯社副總裁 Ron Nixon 說,他會和記者坐下來,讓記者講故事。因為人們都喜歡聽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並且,當記者只講述概念,實際上是在講已經自己加工過的思考結果,而編輯並沒有掌握原始材料。編輯應該先傾聽故事,然後再引導記者思考。
他提到一種做法叫“Line by line”(逐行編輯),就是坐在那兒一行一行地編,有時花費四、五個小時,因為要處理每一個因素。比如,即便記者寫到某人是市長,雖然這是常識,編輯也要看到相關的來源——因為記者出錯的地方總在細節上,因此編輯要逐行、再三確認看上去沒問題的細節。具體到一句直接引語,要看到錄音中的上下文,明白這句話的語境,再判斷在文中是否準確。
坐在百人會場上聽這場近1小時的研討,我會不時感到自己受到的激勵大過經驗點本身,那就是:這個世界上還有這麼多人在用這樣的方式做這件事。專業主義並不過時,並且可能是讓做報道這件事具備意義的唯一方式。
再小的空間里也要做事
最後我想回到最初申請參會的,那個最直接的初衷:我想知道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哪些同行和我們一樣處境艱難,又怎樣克服。為此我去聽了一場名為“如何在艱難的地方做調查報道”(How to Spread Watchdog Journalism in Tough Places)的講座。
來自孟加拉的記者 Hasibur Rahman 說,在他的國家,媒體做很多事都需要走一個官僚主義的流程,得到批准才能進行操作。同時讀者也對媒體缺乏信任。人們普遍對新聞缺乏認知,生產新聞流程是什麼,新聞的力量是什麼。
一位在全球培訓記者的專業人士的發言讓人稍感安慰。她說來自政治和經濟的擠壓,是全球記者都在面臨的挑戰,不只在幾個國家。過去兩年,她訪談了全球各地的數百位記者,問他們是否感到壓力在增加,是否覺得自己在危機中工作,幾乎所有人都回答是。
那在這樣的環境下還能做些什麼呢?其實在這次大會中,一些海外同行,特別是來自亞洲地區的實操案例給了我一點信心。比如上文提到的敘事類播客,其實在國內也有同行嘗試,但在傳播上很難打開局面,也難以組建成規模的團隊。但在印尼 KBR 的案例中,他們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沒有專門的調查團隊,只能在常規工作之餘去嘗試這件事;音頻調查報道節目在當地也缺乏受眾。但他們還是通過宣傳,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這些問題。他們深入大學,和學生就如何製作調查播客做交流;也深入社區,一起在 Instagram 上直播,討論播客背後的故事。總之,他們在嘗試用不同角度將一個播客推向不同社群的新受眾。在尚可操作的層面,問題並不是完全無解。
至於我們都無能為力的層面,也許能用來支撐自己的就是一點信念。本次大會讓我印象最深刻的瞬間,也來自 “如何在艱難的地方做調查報道”的分享。在幾位嘉賓發言後,一位女記者站起來提問,說她來自阿富汗,在2021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後,領導一家名叫“Zan Times”的女性記者編輯部,流亡到了加拿大。
“我們非常痛苦掙扎,”她說,她一方面憂心同事的安全。女性記者、在塔利班掌權的地方生活,晚上她想到這些就常常失眠、做噩夢;另一方面她找不到資金,常常無法給這些冒險工作的同事付工資。有時她挪用自己的錢,但她也有家庭,也要吃飯。她想知道自己還能怎麼辦。
一位嘉賓給她建議:可以把這種處境寫下來。讓編輯部所處的地方——加拿大的人們能更理解她們的困難。建立連接,也許能爭取到支持。但這位嘉賓接着也遺憾提醒,眾籌恐怕很困難,特別是在英語世界外,媒體很難獲得支持。
另一位嘉賓說:“你不是一個人,這棟樓里有2134個人,我們在一起,我們一起工作來保護我們自己。我們會感到孤獨,但我讓自己積極的方式就是,今天我們是2134個人。”
這句話讓我想到了半年前,香港一位新聞傳播學教授李立峰在新書《閱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中寫到的一段話:總有人問我,還有人願意學新聞做新聞嗎?但事實是,即使在全世界環境最惡劣的國家,也有人還在做新聞。
作者於月,非虛構寫作者,2023年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獎學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