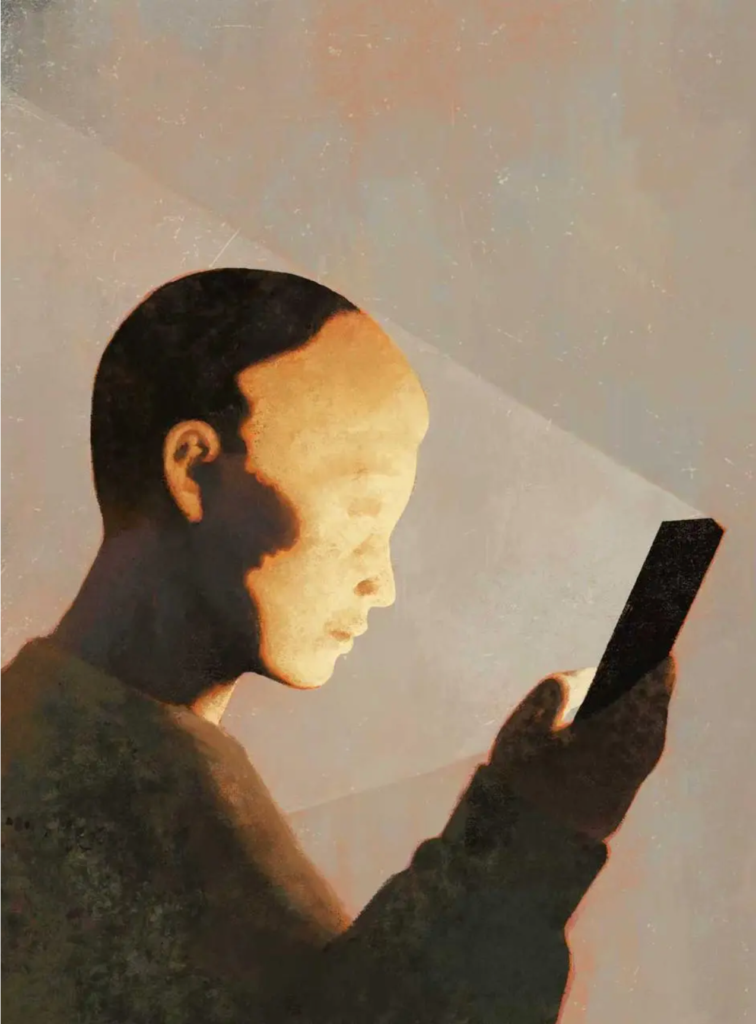越來越多女性擔當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但她們賺得總比男人少。《穀雨數據-騰訊新聞》整理了多份研究報告和統計數據,了解在平台系統、現實生活等困境之下,女騎手和女司機如何難以幹得跟男性一樣多,以及即便她們幹得比男性多,也難以獲取較高的收入。
8月11日,江蘇省常州市芳茂山公園的一個涼亭在風雨雷電中坍塌,造成至少6人死亡、10人受傷,受害者大多是來自外地的務工者。事故發生翌日,倒塌涼亭的廢墟已被清理乾淨,但涼亭為何抵擋不住如此常見的天氣狀況,依然未有答案。《三聯生活周刊》採訪了事故親歷者,還原當日事發經過,還向專家了解涼亭一類建築因何久缺施工質量監管。
在中國,被官方稱為“殘疾人”的有超過8500萬人,但他們難以被公眾看見。有殘疾人解釋,他們甚至過不了家門口那條太陡的坡道,而投訴、整改過程太多波折,遑論要上班、上學和走進社會。《澎湃人物》的報道,了解了殘疾人一個卑微的願望——出門。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8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為什麼女騎手、女司機賺得總比男人少?
出品:穀雨數據-騰訊新聞

圖:互聯網
越來越多的女性擔當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但為什麼女騎手和女司機賺得總比男人少?
從美團研究院的調查數據來看,2020年平台內的女騎手占騎手總數的7.4%。根據相關學者的研究結果,到2021年,北京的女騎手佔比達到16.21%。2021年滴滴的報告則顯示,自滴滴成立以來,237萬女性司機曾在平台獲得收入。
然而,相比男性,女騎手、女司機的收入相對較低,即便她們付出的努力一點也不少。首先,外賣騎手的收入取決於訂單量,但女騎手很難比男騎手跑得更多,加上梯度計費的方式(即跑單越多,單價越高),跑單更多的男騎手往往單價也更高。研究數據顯示,女騎手最多收到的單價5元以下的訂單(比率約45%),而男騎手的訂單最多集中在5至8元區間,甚至有三成男騎手的單價是在10元以上。
粗看之下,外賣行業遵循多勞多得的原則,女性收入較低是因為她們幹得少。事實是我們必須正視她們面臨的具體問題,以及身處的結構性困境。研究調查顯示,女騎手也有“單王”,即所在站點的當月接單量第一名。不過,研究團隊接觸到的三位女性“單王”騎手,跟大多數女性騎手不同,都比較年輕,年紀在23到26歲,而且都未婚未育。這三位女性“單王”每天平均的勞動時間長達11個小時,比男性“單王”要多1到2個小時;也就是說,女騎手可以幹得跟男騎手一樣多、甚至成為“單王”,前提是她們很年輕、不需要照顧家庭,才能付出更長時間的勞動來換取收入。研究數據顯示,這些年輕女騎手是少數,在全國女性外賣騎手中,七成都是30歲以上、兩成是40歲以上。
那麼,為什麼仍然有越來越多女性投身外賣和網約車行業呢?聯合國婦女署的數據顯示,無償勞動在中國女性中非常普遍。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明顯更有可能選擇靈活就業,利用碎片化時間從事靈活的工作。對於一些女性來說,雖然她們送外賣、開網約車時遇到過很多系統困境,但因為能同時滿足照顧家人、獲取收入的現實需要,甚至可以帶來一些和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依然算得上“當下少有的較優選擇”。
公園涼亭坍塌致6死10傷:倒在風雨中的外地務工者
出品:三聯生活周刊

涼亭坍塌後的現場。圖:受訪者提供
8月11日,江蘇省常州市這一天十分悶熱,一整天都是那種要下雨又沒下雨的感覺。晚飯後,鄭心琴跟大兒子孫俊晧騎着電動車去往芳茂山公園,鄭心琴想趁閑暇帶外地念大學、暑假過來短聚的兒子到處轉轉。芳茂山公園是橫山橋鎮最大的濕地公園,圍湖而建,佔地350畝,去年11月才開園。母子兩人從西側入口入園,很多飯後散步的人,三三兩兩結伴,帶着孩子,十分熱鬧。
母子繞湖走了半圈,此時開始起風。孫俊皓說:“走吧,要下雨了。”兩人繞到公園西南角,出去要經過石橋上的涼亭。剛走過涼亭30多米,大顆雨滴開始飄落,砸在身上冰涼。因為擔心感冒,母子兩人又跑回了涼亭,涼亭當時已經聚集了20多人。孫俊皓站在東北角,靠近橋面欄杆,母親在他左後方半米的位置。
十來分鐘後,雨勢漸小,孫俊皓給父親打了視頻電話,說再等一會兒就走。可突然風雨又大了,伴隨着閃電,一會在東邊,一會在西邊,感覺就是老圍着涼亭閃。就在這時,亭頂“咔擦”一聲脆響,“有點像木頭斷裂的聲音”,亭內燈一下滅了,隨即傳出“轟隆”巨響。亭子坍塌,巨大蓋有琉璃瓦的木質屋頂卻十分完整,像鍋蓋一樣蓋在人們身上,裂開的木頭像刺一樣伸出去,破裂的瓦片像碎掉的碗一樣鋒利。
只有五個人在亭子坍塌前一瞬間跑得出來。廢墟上,孫俊皓以粗啞的哭聲喊着“阿媽、阿媽”。亭子往西南方向坍塌,剛好在他腳下空出鍋蓋那麼大一片地方,母親卻已倒在他腳下,蜷縮着,半個身體壓在亭子底下。直到9點半左右,鄭心琴被送到常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接近凌晨3點,醫生告訴家屬,鄭心琴被有搶救過來。連同鄭心琴,這次事故至少造成6人死亡、10人受傷,受害者多來自外地,在常州務工,芳茂山公園是他們務工之外,為數不多的能夠消遣逗留的地方。
事故發生翌日,倒塌涼亭的廢墟已被清理乾淨,原來涼亭所在的橋面用雨布蓋了起來,彩鋼圍起一圈。國家一級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岩土工程師陳宇(化名)告訴《三聯生活周刊》,由於涼亭不住人,屬於建構物而非建築物,在實際施工時通常交由景觀園林公司負責,他們再分包給小型承包單位。涼亭這類單體建築面積小於5000平方米的新建建築,毋需進行施工圖審查。缺乏監管之下,包工頭可能隨便找七、八個工人就能開工,出於成本考量更會偷工減料,“很多公園涼亭開裂、沉降十分嚴重”。
出門的權利
出品:澎湃人物

門前的坡道。圖:受訪者提供
張辰,25歲,大學本科學歷,正在北京海淀區中關村一家互聯網外企實習,等待一個轉正名額。在中國,姓張的有超過9500萬人。
與此同時,張辰是一名腓骨肌萎縮症患者,自幼生病,日常完全依靠輪椅出行。在中國,被官方稱為“殘疾人”的有超過8500萬人。
如果將生活中遇見各種特質的人視為一種隨機事件,按照統計學的大數定律,遇見19名姓張的人跟遇見17名殘疾人的概率是一樣的。那麼,為何我們經常能遇見姓張的人,卻甚少遇見殘疾人?殘疾人到底在哪兒?
張辰的回答是:摔倒在坡道上。由於家門前的坡道太陡了,遠遠超過了國際標準,張辰每次坐輪椅下坡,都會“像溜冰從山上滾下去”。他曾經兩次重重地摔倒在地。
過不了家門前的坡道,就無法出門通行。張辰聯繫過街道殘聯、社區、12345(政務服務便民熱線)⋯⋯至今,他維權即將滿一年,坡道的改造依然因法理和觀念問題而陷入僵局。8月底,張辰住處的租約就將到期,他不知道還能不能續租。
對於張辰這樣嚴重的肢體殘疾青年而言,坡道是與社會連接的第一座弔橋。沒有這座弔橋時,他曾無數次像現在這樣卡在家門前,望着學校食堂、教學樓等公共場所築在階梯上的大門,宛如望着天塹。他想要的,不過是“出門”的權利。
哲學家朱銳的人生最後一課
出品:剝洋蔥 people

2024年春季課堂上,朱銳在講課。圖:受訪者提供
6月初,春季學期的課程收尾,中國人民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跨學科交叉平台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朱銳教授說,最後一節課不要講太沉重的東西,於是從康德談起。
2022年下半年,朱銳確診直腸癌,此後一年因輾轉治療而沒有開課。2023年秋天,他久違地回到課堂,一周一次給本科生講課,上學期講“形而上學的恐懼”,下學期講神經美學。起初,這門課主要是哲學院內的本科生在聽,教室仍有空座。今年春天,朱銳的碩士生可欣在社交平台上發帖,記錄朱銳的課堂片段,標題是“因為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帖子獲得近三萬點贊。此後,課堂“盛況空前”。階梯教室塞進了一百多人,甚至有一排人坐在教室外的走廊聽課。學生們還建了一個線上聽課群,每周直播課堂。到學期末,群里加了近三百人。
最後這一堂課接近尾聲,朱銳總結,個人的生命與宇宙之類的普遍原則間有一種辯證關係,“不管普遍原則多麼浩大,它總有小的一面,私人的一面”。 他強調個人生命的體驗,“要相信你自己的渺小,但不要感到卑微”。
而後他說,他累了:“謝謝大家,到此為止。” 他支撐雙手,有一個小小停頓,再站起身。之前的一堂課上,他提過,作為病人,操控身體是很難的:“比如起床,短則兩分鐘,長則半小時。我要籌劃,手、胳膊、上身先動,再動哪個腳⋯⋯”
打鈴了,最後一節課結束。學生可欣委婉地問朱銳,今天身體怎麼樣?他顯得有點高興:“我跟你說,非常驚險!我今天來這裡前忘記吃止痛藥了,但居然沒那麼疼(…)但是晚上回去還是要吃藥的,否則會疼得睡不着覺。”
這堂課上,朱銳的所有碩博生都在場。當天中午,大家約着給一位即將畢業的學長餞行,朱銳沒有來,但給了經費,讓大家找一個“時尚又高檔的餐廳”。可欣說,這是老師的身體已實難支撐。
8月1日,人民大學哲學院發布訃告——哲學院“傑出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跨學科交叉平台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朱銳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當日下午13時15分在北京逝世。當晚,朱銳的一位學生在朋友圈裡寫下柏拉圖的詩:“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願意變作天空,好得千萬隻眼睛來望着你。”
19歲大學生兼職騎手,消失在外牆磚下
出品:極晝工作室

圖:互聯網
鄧少雄(化名)原來是一名19歲的學生,在西南林業大學計算機專業讀完大一,趁暑假兼職騎手賺錢,減輕同為外賣員的父母的負擔。8月2日傍晚,昆明市區剛停雨,鄧少雄送完海倫先生小區1棟的外賣,走出大堂門口3米左右,被從4層落下的外牆磚砸中身亡。
在兒子送外賣前,老鄧把經驗都教給他,“第一就是遵守交通規則,第二是新手不能同時接超過三個訂單,這樣才有比較寬裕的時間送餐”。老鄧也送過海倫先生小區,從西北側的門進入,有一條電動車和機動車都可以走的斜坡,爬上坡道左拐,電動車會停在1棟寫字樓大堂的入口,那裡就是兒子這次出事的位置。老鄧每次都進出匆忙,沒想過這裡會有風險。
小區業主梁小清(化名)提到,她早在去年遇到過類似的牆磚掉落事故——當日,她和兒子一起去自己開辦的幼兒園上班,兩人剛走到西側入口,1棟樓一排外牆飾磚砸落在他們身後。梁小清看到,入口外的樓梯台階被砸出了小坑,立即喊來物業清理,要求他們把牆上剩餘的裝飾磚都拆下來,希望能消除風險。
反映問題之後,梁小清記得物業只清走了幼兒園門前的碎磚塊,再派人用竹竿敲了敲剩餘的外牆裝飾磚,說是不存在安全問題。拆除的事沒了下文,梁小清也逐漸忘了那次事故,直到這次有外賣員被砸身亡,而且還是發生在1棟,她再去仔細數過:“外牆磚是從四層左右脫落的。”
有業主翻出群里的聊天記錄,發現最早在2020年3月已曾發生“外牆磚”事故,物業管理人員當時在群里通報過1棟寫字樓的外掛石材脫落。業主根據聊天記錄的關鍵詞統計,2020年至今,1棟外牆磚掉落過三次,2棟掉落過三次,3棟也掉落過一次。
外賣員出事之前,小區業主最後一次提醒物業處理安全問題是在7月27日。當日,一位業主注意到小區公寓樓的牆上再次出現裂縫,大於一塊磚的厚度,於是在業主群發了消息:“3棟樓下快遞站的磚塊,說了一年了,裂得都肉眼可見的斜了!”物業當時回復,說7月29日會展開大檢查。
鄧少雄去世後,老鄧穿着他買的那件外套,去海倫先生小區找過物業。有業主一直想聯繫老鄧一家,要把關於物業不作為的證據提供給他們,但老鄧不願再有更多麻煩,覺得善後的事已經十分吃力,外賣公司那邊的處理還未解決。
從家中偷走一個11歲女孩
出品:正面連接

插畫:陳禹
這是一起複雜但重要的案件。在司法視角中,案情是這樣的:2021年2月,11歲的陳玥(化名)由一名13歲女孩介紹給一名17歲男子,陳玥被性侵。一個月後,她再由一名12歲女孩介紹給一名31歲男子,陳玥再次被性侵。半年後,陳玥遭遇的侵害升級為強迫賣淫。兩年後,13歲的陳玥兩度進入賣淫團伙,並且涉嫌多次暴力侵害他人。
2024年3月,《正面連接》作者洪蔚琳來到河南省鄭州市,在市區西北部靠近陳玥家的一個酒店房間,見到了14歲的陳玥,還跟她一起待了三周。她還見到了陳玥的母親張靜(化名)——張靜很忙,她正在為女兒奔走維權。洪蔚琳和她一起去了三個派出所,因為三個案子分屬不同的派出所。
在當地一周後,洪蔚琳見到了另一個14歲的涉案女孩小雨、她的母親,還有16歲涉案女孩安安的母親。在洪的印象里,兩個同齡女孩的言談舉止頗為相似,而安安母親口中的女兒就像陳玥的複製粘貼版本。她們都提到女孩們在“圈子”里玩——“圈子”是一個由至少十餘名輟學未成年人組成的小世界,他們會相約打遊戲、唱 KTV、吃飯、戀愛、偷電動車,也不時發生暴力、性侵和相互出賣。陳玥在11歲那一年來到了這個平行世界,目睹身邊女孩們也被喜歡的男孩侵犯,也偶爾被打一頓,或者被姐妹出賣給陌生人發生關係。在“圈子”里,這些遭遇被形容為“倒霉”。“倒霉”過後,女孩們哭泣、紋身、拿小刀劃自己,然後帶上滿不在乎的表情繼續在“圈子”里生活。兩年里,三位母親前赴後繼想“撈出”女兒,做出了基於各自理解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比起母親的影響力,女孩們更感到自己是在圈子裡被“朋友”陪伴成長和互相養育的。
為了補充信息和交叉印證,洪蔚琳還拜訪過陳玥的父親、哥哥、17歲男友阿哲、“圈子”里的好友小皓,甚至一名試圖向陳玥購買性服務的嫖客。
經過五個月的採訪和調查,洪蔚琳的報道成形。在她的記錄中,故事是這樣的:在當下,惡意如何通過互聯網接觸一個家裡的孩子,施以傷害(期間家長毫無感知),從家中偷走孩子,送進成人犯罪世界(期間家長回天乏術),直至孩子也成為一個釋放惡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