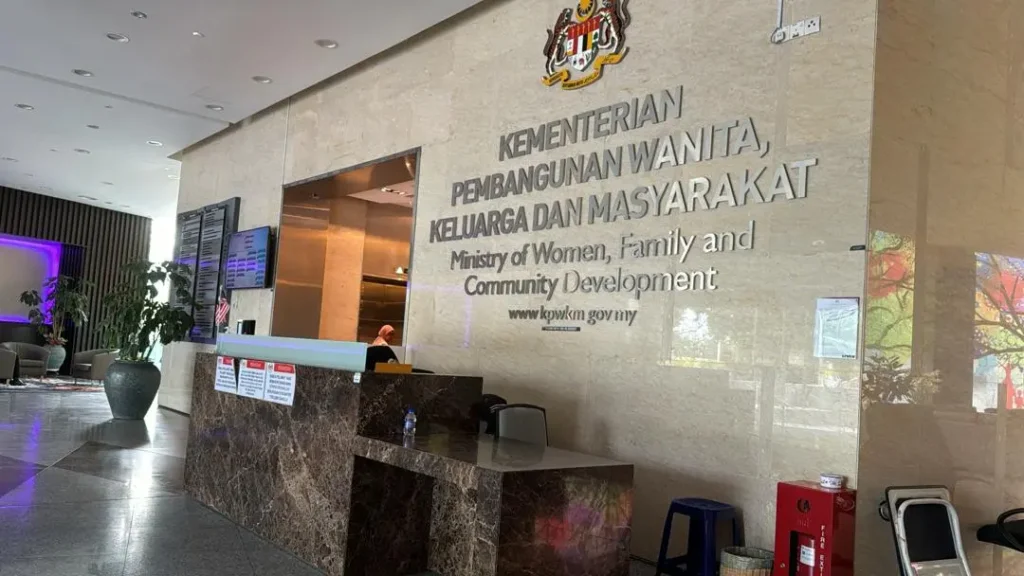圖:互聯網
遊戲代練“胖貓”自殺身亡後,其生前女友譚某被指控詐騙他的錢財,掀起一輪針對譚某的網絡暴力。然而,當地警方調查後認定,“胖貓”的姐姐在網絡上發布“胖貓”與譚某的私聊記錄、找人代寫文案博取網民同情、在平台購買流量擴散傳播提升熱度,目的是要讓譚某“付出代價”。這並非中國網絡上的第一起網暴事件,估計也不會是最後一起。那麼,受害者可以如何告倒一個網暴者?
5月1日凌晨,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梅龍高速公路的一段道路突然塌陷,造成至少48人死亡。《澎湃人物》採訪了多位事故親歷者,重構了事發前後的狀況,還諮詢了多位專家,探討了脆弱地帶道路基建的養護工程困難之處。
負債者越來越多,錢也越來越難催。這是《極晝工作室》訪問的五位催收員的共同感覺。這些催收員當中,有人剛加入這個行業,有人已經做了六年。為了完成業績,有催收員甚至得想辦法幫負債人先找到工作。有催收員更會和負債人一起期待突然“暴富”,畢竟催收員的業績壓力越來越沉重,工資卻越來越低。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5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如何告倒一個網暴者?
出品:新京報

圖:互聯網
遊戲代練“胖貓”(本名:劉傑)在重慶長江大橋上跳江身亡後,他的姐姐在網絡上發出控訴,指他生前遭女友譚某詐騙錢財,事件引起網絡上的熱烈討論,甚至令譚某遭遇網絡暴力。
5月19日晚,重慶市公安局南岸區分局就事件發布警情通報——警方認定,“胖貓”與譚某存在真實的戀愛關係,譚某並未以戀愛為名騙取“胖貓”財物,不構成欺騙犯罪。通報梳理了“胖貓”與譚某的交往、經濟往來等情況,提到“胖貓”的姐姐劉某稱要讓譚某“不好過,付出代價”,與其妹妹商議“就是要讓譚某被網暴”。劉某通過社交媒體賬號多次發布“胖貓”與譚某私聊記錄、轉賬截圖等個人隱私信息,與其妹妹聯繫多人代寫文案,討論如何博取網民同情,還在平台購買流量擴散傳播提升熱度。警方認為,劉某的行為導致譚某被網友攻擊辱罵,出現多起威脅譚某人身安全的言論,嚴重影響譚某正常生活,並且造成網絡空間秩序混亂。
中國早在2008年出現較為公眾熟知的“網絡暴力第一案”,自此網暴與互聯網的發展糾纏在一起。2018年,德陽安醫生和丈夫在泳池裡與13歲男孩發生衝突,事後經過網絡媒體的傳播,安醫生遭到人肉搜索;2022年7月,染了粉紅色頭髮的鄭靈華在爺爺病床前分享收到研究生錄取通知書的喜訊,因發色被“造黃謠”;2023年5月,武漢一小學生在校內被撞身亡,其母親因容貌衣着飽受網絡暴力⋯⋯
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於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共20條,其中指出對於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應當依法嚴肅追究,切實矯正“法不責眾”錯誤傾向。要重點打擊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對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應當體現從嚴懲治精神。
在《指導意見》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提供一組數據,他表示,近年來,出現了涉及侮辱、誹謗刑事案件數量明顯增長,但有罪判決比例很低的巨大反差。周加海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自訴人收集證據時存在困難,另一方面,也與侮辱、誹謗刑事案件的公訴標準缺乏細化指引、“門檻過高”有關。對此,《指導意見》明確了刑事自訴案件轉公訴的路徑。
然而,如何告倒一個網暴者?如何維持網絡空間的秩序?多位學者表示,儘管《指導意見》為有效打擊網絡暴力提供了規範,但網絡暴力的治理之路依舊漫長。
梅大高速涉事邊坡:脆弱地帶與養護之困
出品:澎湃人物

部分車輛車頭引擎處缺失,留有明顯燒毀痕迹。 圖:封面新聞
“橋斷了,好多車掉下去了,不斷的爆炸聲。我們離死亡就差100米。” 5月1日凌晨2點27分,有塌方親歷者在微信朋友圈發布圖片——夜幕下,大片濃煙在火光映照下被染成紅色。
當日凌晨2時10分許,中國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梅龍高速公路(梅大高速段)東延段 K11+900 一處道路突然塌陷。截至5月2日下午2點,官方發現23輛車陷落,48人死亡,另有3人的 DNA 待進一步比對確認,沒有生命危險的傷者也有30人。
黃建度當時與家人從深圳龍崗回梅州老家,由他的女婿自駕。行駛至梅大高速路段時,車上乘客正在睡覺,車身猛地一晃,他們一下驚醒。據他們憶述,當時身後的路邊欄杆正往下陷,右車胎卡在開裂的路縫裡爆胎了,黃建度的女婿仍踩緊油門加速,車子在劇烈的搖晃中險些撞上欄杆,最終衝過了陡然塌陷的路面。
衝過塌方路段一、兩百米後,黃建度一家緊忙下車往回趕,舉起手電筒向來車揮手示停,但仍然有車輛墜入坑裡。情急之下,黃建度鑽過身旁的欄杆,從對向車道跑到塌方前段,跪下逼停了欲前行的十幾輛車。他向《澎湃新聞》回憶說:“我下跪欄車的時候,塌方(處)還沒有火,因為沒有火光和濃煙,開過來的車都看不清前面的情況。大概掉下十輛車之後,掉了一輛電車下去,開始起火了。”
《澎湃新聞》引述知情人士稱,今次塌方路段曾在2022年8月出現水毀病害,坡面溜塌、急流槽損壞,此後進行過加固和完善排水,修復工程從2023年4月到9月分批建設完成。此外,記者走訪獲悉,在事發前這一路段或周邊曾經多次巡查養護。有養護人員稱,在塌方前一小時左右經過涉事路段,未發現路面異常。
不過,從事岩土工程、邊坡穩定性分析研究的學者陳志鵬告訴《澎湃新聞》,山區公路一般不會進行特別加固,“要平衡安全和經濟”。高速公路設計會考慮50年、100年一遇的暴雨、洪水,但遭遇極端惡劣天氣,也可能超出公路的承載能力。陳志鵬稱,這次事故提醒邊坡工程地質災害防治水平有待提高。
在行業內,邊坡路基的巡護也受制於資金、人力、技術等,即使是邊坡位移智能監測設備 GNSS 也可能有監測盲區。長安大學公路學院副教授李家春就向《澎湃新聞》指出,若塌方是突發的,那 GNSS 設備可能來不及預警。
他們在工廠或跑外賣的路上,接起催債電話
出品:極晝工作室

圖:東方 IC
“跟你聊一聊吧。”電話那端,30多歲的中年男人突然願意說了:“我把實際情況跟你講,能不能延長(還款期)?”為了得到中年男人的回應,催收員蘇毅少說打了半個月的電話,之前對方一直不耐煩、說一句“在工作”就掛了。這次聊了半個小時,蘇毅終於聽出了他的請求。
中年男人在廣東省生活,本來靠維修手機糊口,後來開始打零工,穩定的時候跟妻子加起來月收入能有7000到8000人民幣。租房一項就得花3900元,佔了收入的一半,加上孩子剛上初一,也是一筆不少的開支。不穩定的時候,他就貸款付房租,10000元的貸款已經逾期將近兩年,他想再拖一拖。
最近兩個月,蘇毅每天打出50通電話,對方大都是這種“客戶”。蘇毅當了催收員五年,目前為面向普通人貸款的互聯網消費金融平台當催收員。在貸款表格上,債貸人填報的貸款理由往往是“房屋裝修”、“日常生活”、“出行旅遊”等,但實際上電話溝通之下,發現他們有的是貸款去創業的;有的是疫情後公司倒閉,貸款給員工發工資的;有的是已經被公司欠薪一、兩個月,只能借錢去還房貸、車貸的。
負債人的話真假難辨,但蘇毅憑經驗做過總結,能從對方語氣聽出是不是真有苦衷:“那些含糊其詞說自己沒錢的,或者就說一句‘我有錢了就還’的,大都是撒謊。”在催收員眼裡,每個負債人都有“賬齢”,即逾期還款的時長。蘇毅負責的“中端”負債人,是還債一年以上、兩年以內的,90%都是30歲以上的“普工”(即從事普通工種),經常在跑外賣、送快遞的路上,或者在工廠裡邊焊接邊接起電話。
逾期還款的人各有各的苦悶,催收員則坐在格子間里,每天打十幾個電話,聽不同人的生活遭遇,另一方面千方百計令負債人儘快還款,抓住痛點、懷柔政策、共情等策略層出不窮。一個江西省的中年男人離異後帶着女兒,貸款做餐飲,卻賠了錢,跟催收員說自己堅持不下去了;催收員跟他加了微信,還給他點了外賣,勸他“先把自己日子過好”。後來,那個中年男人真的還了錢。
《極晝工作室》訪問了五位催收員,有人剛加入這個行業,有人已經做了六年。他們的一個共同感覺,是負債者越來越多,錢也越來越難催。為了完成業績,有催收員甚至得想辦法幫負債人先找到工作。
上個月,蘇毅在他公司20多人的催收小組裡,業績排名倒數第二。打電話時,一個負債人說了一句氣話:“等我中了彩票再還錢!” 蘇毅忍不住和這個負債人一起期待“暴富”起來,今年也開始買彩票,畢竟他的催收員工資也太低了。
幼兒園轉身變成養老院
出品:冰點周刊

4月16日,山東濟寧,一所”老幼融合”的幼兒園,老人看着孩子表演節目。圖:焦晶嫻
周鑫今年24歲,在山東省濟寧市一家教育集團的幼兒園當教師,沒想到工作從領着孩子做拍手操,變成領着它人做八段錦。這家教育集團去年以來關閉了三家幼兒園,仍在運營的幼兒園也大多縮減了班額。與此同時,集團開始向“人生的另一頭”謀求生路——開設養老中心。
集團老闆于波開了20多年的幼兒園,做出轉型的決定並不容易。他計算過,招生情況如此不理想,今年暑期後大班的孩子一畢業,旗下幼兒園將會有大約40位教師面臨失業。新開設的養老中心選址在老城區,位於某小區居民樓的一層,提供日間康養和休閑服務,做理療、打乒乓球、上手工課等,服務對象是60歲到75歲的“活力老人”。
眼下,老年人會員仍然不多,老師絕大多數回到幼兒園工作,但周鑫卻選擇留在養老中心。她回憶,2017年“全面二孩”政策剛施行,“學前教育”成為了熱門專業。2020年畢業時,周鑫的不少同學轉行做網絡主播、開麻辣燙店等,周鑫還是到了幼兒園工作。剛入職時,她並不需要幫忙招生宣傳;兩年後,她周末還要加班進小區做“地推”。
2020年,中國全國人口出生率跌至1978年以來的新低。教育部和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23年在園幼兒較前一年減少近535萬人,幼兒園則減少1.48萬所。周鑫所在的山東省濟寧市,一家家民辦幼兒園被饅頭鋪、火鍋店等取代,環城西路附近的“幼兒園一條街”上,一些幼兒園已經暫停招生,地圖上顯示為它們“疑似關停”。
幼兒園園長楊娟從事幼教行業20多年。她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20年前第一批民辦幼兒園剛興起,進不了公立園的孩子紛紛湧入私立園,有些家長整晚排隊報名;到了現在,“有一個孩子報名,全園就想放鞭炮”。
相反,老年服務行業的熱度正在持續增長。在山東省,2020年60歲或以上人口佔比20.9%,高出全國水平2.2個百分點。在濟寧市最大的城區任城區,有民政局養老科工作人員指出,近一、兩年不少人來諮詢養老機構的建設補助,目前區內設有30多家養老機構,新開不滿一年的約佔三分之一。
下一步,于波計劃把旗下一家幼兒園內閑置的樓房改成養老服務中心,讓老幼共享食堂。他認為,孩子和老人吃的差不多,都是“碎、爛、軟、少油、少鹽”,來送孫輩的老人可以就近娛樂、上課,不用着急跑回家做飯,晚上接了孫輩一起回家。
目前,于波的養老中心還沒有盈利,店鋪會員平均每日支付3元,無法抵銷理療材料、人力、房租、水電費等成本。不過,他有耐心等待:“我們現在就是讓老人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在等這個市場。”他認為,隨着第一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60後老人退休,中高端養老市場潛力很大。60後的消費觀念與50後不同,而且他們的知識文化水平更高、孩子是獨生子女,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也更高。
就業務轉型,于波設定了三年周期,希望在過程中幫助幼師團隊再就業,並且增加幼兒園的附加值——比如幼兒入托報名,贈送老年食堂飯卡、居家養老上門服務。“幼兒園只能服務孩子3年,但養老能服務老人幾十年。我們將會陪着他們慢慢變老。”他說。
智能貓屋撤出長沙:流浪貓,怎麼管?
出品:北青深一度

兩隻流浪貓。圖:拾圓
2024年4月,長沙的貓屋申請人鄭儀接到“街貓”APP 的官方來電,被告知因為平台運營困難,當月30日之後會將全部街貓設備撤離長沙。申請人若想保留貓屋,可以每月228元的費用租下,但補糧、充電、維護等工作需要由申請人自行負責。與此同時,申請人租下貓屋之後,仍然可以在平台進行直播,以眾籌貓糧,用戶在直播間給貓屋投喂貓糧所花的愛心幣可以返現給申請人。
“這讓我感覺它(街貓 APP)變成一個純商業性質的東西了,這才是我不滿的地方。”鄭儀告訴《北青深一度》,她選擇了不續租。
街貓是由廣西哈寵公司開發的一個流浪貓關愛平台,其自主研發的“街貓智能流浪貓管理貓屋”通過連接 APP,能夠實現貓屋智能喂水、喂糧。自2022年初,街貓開始在上海鋪設貓屋,次年4月 APP 正式上線。
隨着“新鮮哥”(一隻流浪貓。貓屋裡面掉落的貓糧一旦超過5秒,它就寧願餓着也不吃,於是網友給它取了這個名字)等“明星”流浪貓在短視頻平台走紅,街貓也被推到了億萬網友面前。在街貓 APP 直播間里,流浪貓成了主角,人們通過攝像頭可以實時看見流浪貓們匍匐在貓屋中“等待出糧”的憨態。同時,用戶只需要在手機屏幕上動動手指,充值愛心幣,就能兌換貓糧實現投喂。
在街貓系統內,除了申請貓屋,還可以成為認證志願者“貓貓俠”,協助申請人維護貓屋。如今,街貓已在上海、杭州、廣州等12個城市設有1.3萬多個貓屋。
在接到撤機的通知後,鄭儀最不能理解的,是“長沙地區街貓運營困難”的理由。在她看來,街貓的運營成本並不高。貓屋自落地起,所有的衛生維護都由她和“貓貓俠”負責,鄭儀基本上隔一周就會清潔一次。街貓工作人員只在設備電量不足或出現故障、儲糧箱需要補糧時,才會進行現場維護。貓屋有時會有流浪貓得病,也是由申請人和“貓貓俠”們負責救助。鄭儀和“貓貓俠”們曾遇到過一隻患有口炎的流浪貓,他們將它送醫並墊付醫藥費,事後才通過街貓APP的“貓友圈”發帖、微信群宣傳等方式向愛心人士籌集了1500元的醫療善款。
隨着愛貓人士與街貓平台的連接加深,他們慢慢發現諸多問題——貓糧定價過高,運營過度依賴用戶“為愛發電”、在貓屋附近發生多起虐貓事件……人們開始反思,這樣的庇護所,真的能長久庇護流浪貓嗎?
短劇編劇,被流量操控
出品:剝洋蔥 people

2024年4月,一部女頻短劇拍攝現場。圖:受訪者提供
2022年8月,劉笑天辭去了某網站文學板塊總編的職位。從事網文行業近20年,他發現視頻在近年來取代文字成為更容易被接受的傳播媒介,也漸漸有同行將自己的 IP 改編成短劇,並且收到了不俗的市場反饋。在他看來,“這是短劇的雛形”。
經過兩個月的市場調研,劉笑天也成為了一名短劇編劇。他將短劇視為一個流量高速變現的生意,不是創作,而是商品,而且“和衣服襪子沒有什麼區別”;他視自己為一個產品經理,而不是文學創作者。“說白了我們就是服務業,肯定要找准用戶痛點,把客戶服務好。用戶需要什麼,我們生產什麼。”
2023年年末,短劇進入主流視野,曾經寫長篇電視劇的、寫網文的、為新媒體撰稿的人們紛紛進入短劇劇本創作領域,期待這個嶄新的行業回饋給他們流量、名聲和財富。像劉笑天,入行不到半年,稿費已經上漲到兩萬元,又僅在半年之後,稿費因為資本入局而再次上漲,月收入很快就超過了十萬元。
不過,不少短劇編劇總結出了一套順滑的萬能流量公式,“酒色財氣”、“互搧巴掌”等劇情精準地踩在觀眾們的情緒點位上。編劇們在其中經歷着自我拉扯:“我也受不了其中狗血的部分。” 事實上,早在2022年11月,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網絡微短劇管理 實施創作提升計劃有關工作的通知》,其中寫明要對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格調低下、審美惡俗等內容的“小程序”類網絡微短劇開展專項整治。
《剝洋蔥 people》引述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媒介研究學者劉陽表示,他也曾在自己的首頁刷到過這類短劇。在他看來,“短劇以一種誇張的情緒俘獲觀眾,在目前的確是泥沙俱下”。他建議,在對短劇進行規範化管理,將劣幣驅逐出市場的同時,也應該推進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不是下沉市場的觀眾只愛看這個,每一個人都有獲取尊嚴感,追求崇高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