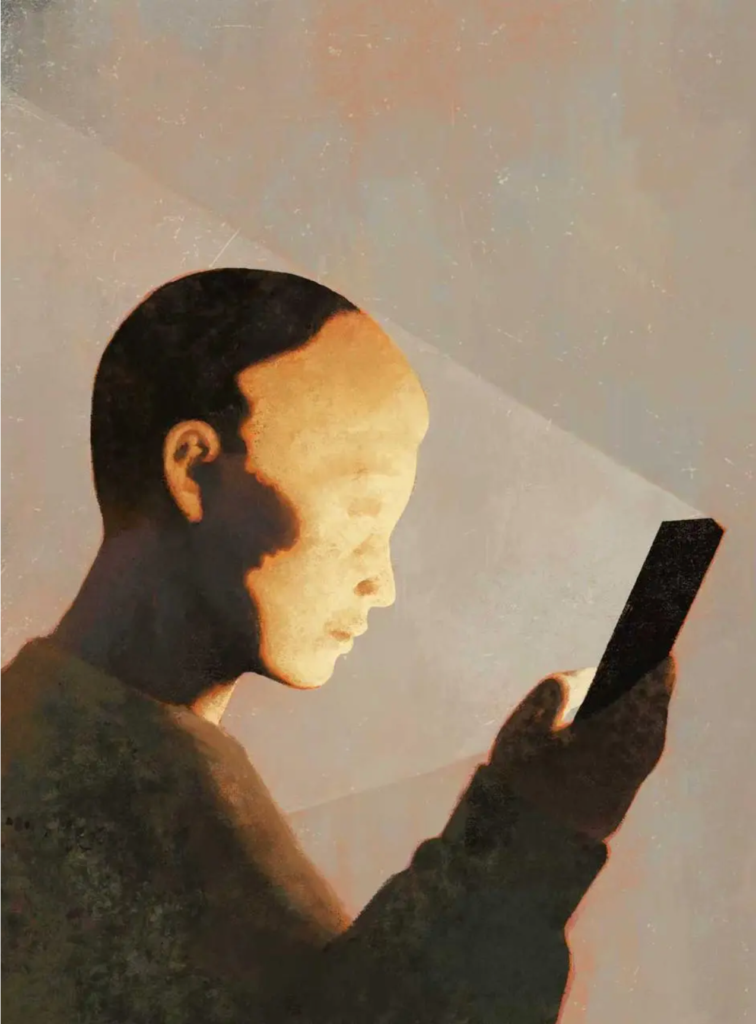北青報總編:深度報道如何突破?定目標、找路徑、緊扣事實
從自閉症少年雷文峰到山東“刺死辱母者”於歡,近期一系列揭露社會痼疾的深度報道引發了廣泛的輿論關注,促使官方採取行動,也讓公眾和業界重新開始探討深度報道的價值。深度網經授權轉載RUC新聞坊(微信ID:rendaxinwenxi)對《北京青年報》總編輯余海波的專訪,看他如何定義深度報道,以及對做出突破性的深度報道有何心得。
原文:《北青報余海波:深度報道的關鍵在於突破 | 媒體人說》
1.如何定義深度報道與新聞價值
我們很難構造一個具體量化的標準或模型去定義深度報道,但通常而言,深度報道主要是基於事件和人物,尤其是基於社會事件的報道。
“深度”二字的內涵在於,首先,報道展開的事實足夠長,對事實掘進得足夠深;其次,報道在輿論場有影響力,如同一顆石子扔進水裡,激起的漣漪比別人要大要深得多。
新聞學課堂上說的新聞價值是指新聞的顯著性、重要性、接近性等等,這些概念在實戰中有時不是那麼容易把握。在實際操作中,新聞是新近發生的巨大變化,新聞價值的大小與事實變化的落差正相關。
文科生比較喜歡概念化的東西,但我更喜歡數據化的語言。一個新聞事件積累的“W”最多,就最有價值。新聞事件發生之後,公眾都展現出很多疑慮,不停地發問,那麼這是一件有新聞價值的事。如果這件事能被一眼看到頭,就沒有什麼價值。
 案例:3月17日,北京市出台樓市新政。媒體如果要做報道,一定會這麼思考:這個政策的核心是什麼?跟以前的政策相比有什麼變化?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會造成市場上什麼樣的變化?它的具體細節是什麼?為什麼出台這個政策?報道一定會呈現這幾個問題,這就是樓市新政的新聞價值。
案例:3月17日,北京市出台樓市新政。媒體如果要做報道,一定會這麼思考:這個政策的核心是什麼?跟以前的政策相比有什麼變化?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會造成市場上什麼樣的變化?它的具體細節是什麼?為什麼出台這個政策?報道一定會呈現這幾個問題,這就是樓市新政的新聞價值。
新聞價值的另一方面在於新聞事件的影響力。有價值的新聞事件一定能夠激起、影響、改變某些事。激起,就是事件本身突然帶來熱度,比如突然在各個社交媒體刷屏。影響,就是擴展一件事的輿論捲入規模,在短時間內讓更多的人了解一件事。改變,就是改變原有的意見走向,改變受眾對某件事的原有認知。真正好的深度報道一定是三者之間的重疊。
2.深度報道的關鍵在於突破
 深度報道的操作流程並不特殊,也是選題+突破+採訪+文本+傳播。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就是突破。
深度報道的操作流程並不特殊,也是選題+突破+採訪+文本+傳播。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就是突破。
記者想要突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確定突破目標。
案例:2012年7月13日,北青報刊發《薊縣大火網傳“百人名單”調查》。天津薊縣萊德商廈突然起火後,民間流傳着一份宣稱死亡人數遠高於官方認證人數的“百人名單”。派去事發現場的記者滿羿深入各個村子,進行打聽,最後破除了謠言。滿羿共花了5天時間,深入20多個村子,最遠到離薊縣180公里大港油田,利用種種方式證實證偽,發現100人名單裡面有重複統計的現象。
如果在薊縣大火後做一期深度報道,記者的目標是什麼?就是“死亡人數到底有多少,真相是什麼”。我們藉助了“百人名單”這個公眾最關心的點,但記者首先要探尋的,一定是事實本身。
第二件事是尋找路徑。路徑就是採訪時的“突破路線圖”。
案例:2015年7月,一個自稱“釋正義”的人舉報少林寺方丈釋永信有兩個私生女,其中一個還是與少林慈幼院院長釋延潔所生。負責調查此事的北京青年報記者去安徽走訪了釋永信的老家,老家的鄰居證實,其中的一個所謂“私生女”是釋永信的侄女。記者在河南商丘找到了另一個突破口,人證物證顯示,釋延潔2004年就做了子宮切除手術,不可能懷孕。在北大找到的證據也顯示,舉報信中所稱釋延潔“生子”的時間,她其實正在北大進修。所謂與釋延潔所生的這個“私生女”也不存在。
記者在多地進行採訪,找到了這些證據,真相也就浮出了水面。沒有證據,核心事實的拼圖就無法完成。採訪時的關鍵人、事就是突破路徑,路徑就是要完成呈現核心事實的必要充分條件。
這幾年輿論多次反轉的現象越來越多,作為專業的媒體人,新聞的核心事實容不得半點錯誤。
3.怎樣做好深度報道?
做深度報道,首先需要慢慢積累,加深對時事、對這個世界的理解。二十多歲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做好深度報道難度很大。第二,要拼盡一切去突破。在新聞的時效性和深度上,記者始終面臨著與同行的競爭。第三,深度報道的文本不必花哨,要着重於陳述事實、評估事實。最後一點,控制你的情緒。所有新聞事件過去之後,能經得起反覆審視的,只有事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體,記者的情緒不一定能代表採訪對象,不一定能符合原生事實,不一定能說服受眾。事實上,受眾最關心的也只是事實。
寫新聞不是寫散文,寫新聞也不是寫美文。用最簡單、最簡短的話去呈現事實,傳播事實,就夠了。
Q&A
Q:您如何看待自媒體?最近有篇文章叫《別被自媒體的情緒牽着走》,說自媒體容易情緒泛濫,我們專業媒體是不是也要注意避免過多的情緒?
余海波:情緒是事實的天敵。在人生的任何階段,我們都一定要剋制情緒,做到平衡與客觀。
最近輿論場出現了兩個變化:第一,基於公共事務發聲的自媒體,它們的持續生產能力出了問題。第二,自從自媒體出現之後,輿情反轉的次數越來越多。這反映了大多數自媒體偏重商業利益,缺乏公共性。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未來的新聞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媒體不能基於公共價值做出判斷,對公共事務進行客觀公允的報道,這個社會就會出問題。
Q:騰訊等新媒體的生產效率非常高,而且它們的報道結合了視頻、音頻等等更加受讀者喜歡的表現形式。這樣的形勢下,傳統媒體應該怎麼應對?2014年,網易、今日頭條等媒體開始與各報社合作,面對這樣的形勢,《北京青年報》應該做什麼?
余海波:當今媒體行業的悖論在於,今日頭條、騰訊等網絡媒體對傳統媒體有致命的殺傷力;可是如果傳統媒體死了,網絡媒體沒法依靠那些自媒體來生產高質量的內容。在真正嚴肅的新聞報道上,傳統媒體有着自媒體無法企及的影響力。所以我們的新聞院系要培養更專業的人才,做更高質量的內容。同時我們也很樂意與網絡媒體展開合作,讓我們這些專業媒體人找到一個新的舞台。
不管新聞怎麼變化,它的本質永遠不變——無非是發現事實、記錄事實、呈現事實、傳播事實。融媒體、VR、算法之類的,都只是技術手段。
 Q:深度報道發在紙媒上和發在網媒有什麼區別?網絡媒體帶來了碎片化閱讀的趨勢,會不會比紙質媒體缺少了一些本質的東西?
Q:深度報道發在紙媒上和發在網媒有什麼區別?網絡媒體帶來了碎片化閱讀的趨勢,會不會比紙質媒體缺少了一些本質的東西?
余海波:在網上搞深度報道,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深度報道一定要走向網絡,因為我們所有的人都在網絡生活中。紙媒總有一天要消亡,報紙這種載體要消亡,它們都有自己的命運。
現在傳統媒體出現的問題不是採訪和突破,不是內容,而是變現。一個在社會化大生產專業分工的年代裡,每一個專業分工,都必須完成“生產-變現-獲取再生產的原料”這樣一個閉環。可是現在傳統媒體的閉環被打破了,只能生產,無法變現。我們給網媒供稿,一篇稿子只能拿幾塊錢。
Q:幾十年以來輿論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高校的新聞學教育體系變化並不大。教育該怎麼應對現在的媒體行業形勢?經歷了傳統教育模式的新聞系學生走入工作崗位,會不會水土不服?
余海波:新聞學需要學術做得好的老師,他們對新聞傳播的前沿理論有很多的思考,對社會關係、傳播關係的變化機理有深刻的理解。我們也需要另外一種老師,他們能緊盯並跟隨這個時代的變化。
20多年前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教新聞采寫的趙老師請來他的一個同學給我們上課。後者當時是新華社的記者。他說自己剛進社實習的時候,一篇稿子寫了兩個版本,裝在兩邊褲兜里。一邊是按照人大新聞系標準寫的,一邊是按照新華社標準寫的。他首先拿學院派稿子給帶他的老師看。老師一看就說:“不錯,採訪不錯,文字漂亮,但是……”一聽到“但是”,他就從另一邊兜里掏出新華社風格的稿子。老師立刻說:“嗯,這稿子比那稿子好多了。”
在學校里學會的東西,跟你工作後實戰的東西可能不一樣,建議新聞系學生要好好利用在媒體實習的機會。此外,不僅要會采會寫,也要會玩微信公眾號、會運營、會視頻,所有新鮮的東西都儘力去嘗試感知一下,這樣你找工作時命中的概率就高得多。
撰稿/繆昕
編輯/程涵閣(RUC),梁思然(全球深度報道網)
相關閱讀:
余海波現為北京青年報社總編輯。曾任光明日報新聞報道策劃部副主任、北京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編輯。自2012年6月起,擔任北京青年報社黨委副書記、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