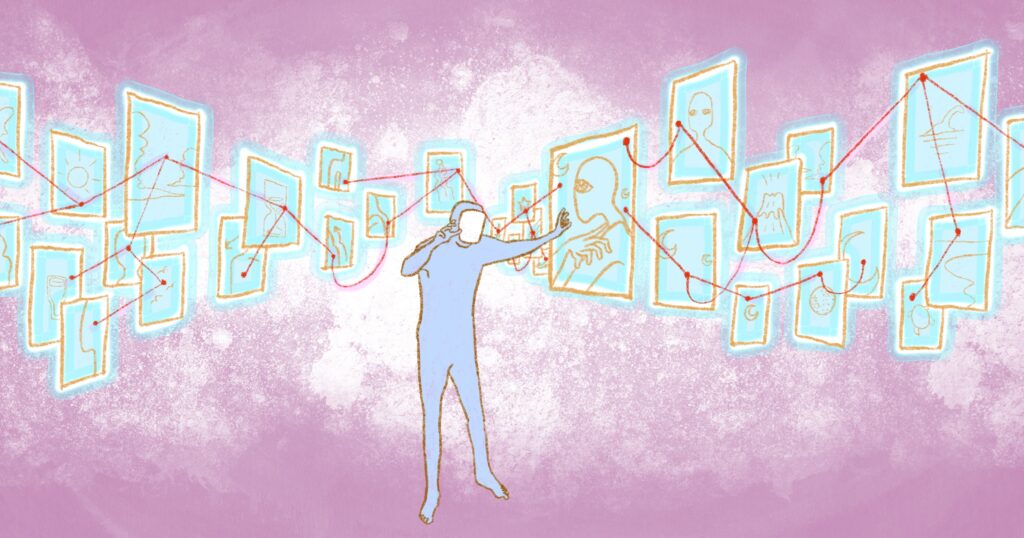墨西哥調查記者、作家、導演迭戈·恩里克·奧索爾諾(Diego Enrique Osorno)
認識迭戈·恩里克·奧索爾諾(Diego Enrique Osorno)的人都會告訴你,他是個永不停歇的人。剛剛採訪完一位大毒梟,他轉身就踏上了橫渡大西洋的航程;花一個月報道毒品戰爭之後,他又用七個月調查託兒所的致命大火;一部關於詩人失蹤的紀錄片剛拍完,緊接着又是一部關於總統候選人遇刺的系列片。在他筆下,無論是聾啞的移民,還是全球首富,都同樣值得被書寫。
奧索爾諾一直沒有停歇。他寫了十幾本書,編劇或執導了多部紀錄片,還進行了無數次的調查報道,講述墨西哥和他出生的城市蒙特雷發生的故事。
作為一名屢獲殊榮的記者,他不僅記錄了毒品戰爭的暴力和墨西哥政府最惡劣的行徑,也記錄了人們的反抗、才華與勇氣。他總能獲得前所未有的採訪機會,這意味着他的報道能夠同時涵蓋權勢階層與受害者,以及兩者之間所有微妙的層次。
他的新書《山中》(En la montaña)榮獲了2023年 Anagrama 非虛構長篇及敘事特稿獎。在拍攝最新項目期間,他接受了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採訪。
GIJN: 您在1999年結識了詩人薩穆埃爾·諾約拉(Samuel Noyola),20年後又為他的失蹤拍攝了一部紀錄片。您從年少時就開始關注薩帕塔運動,如今它又成為您最新著作的核心內容。是否存在一些您始終無法放下的主題?
迭戈·恩里克·奧索爾諾(以下簡稱 DEO):我的青春期是在1990年代度過的。在那十年里,隨着冷戰結束,墨西哥乃至全世界都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在我人生的那個階段,也是我們國家那個特殊的時刻,我面臨著許多衝突、困境、抉擇和揮之不去的“幽靈”。作為一名記者,我們的工作就是關注當下,因此我一直致力於理解現在。但我始終將那個十年里出現的種種問題,作為理解當下困境的指南針與參照。
GIJN: 隨着時間的推移,您運用了不同的工具來報道這些故事。從早期對詩歌的熱情,到學習“crónica”(長篇敘事報道)的寫作技巧,再到您在紀錄片製作方面的大量工作。您是如何選擇這些不同敘事方式的?
DEO: 我想我是一個失意的詩人,而新聞工作讓我保持了理智,給了我一片可以耕耘的土地,一個可以探索的空間。我對調查性報道,尤其是“crónica”,特別感興趣。對我來說,它意味着不僅能深入探究事實和事件本身,還能挖掘這些事實背後的意義與超越性。我感興趣的是,而且我也認為特稿寫作始終要求的,是從調查轉向沉浸。在開口和動筆之前,我總是努力地多聽、多看。我也喜歡“crónica”的視聽形式,也就是紀錄片。視聽世界有另一套語法,即圖像的語法。對我而言,它是一種對話,一種探索,其靈感來源於現實中那些對我至關重要、讓我痛苦、也讓我感動的事情。
GIJN: 您的訪談描繪了處於社會兩個極端的人物,從您的叔叔——一位名叫赫羅尼莫·岡薩雷斯·加爾薩(Gerónimo González Garza)的聾啞移民,到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在刻畫這些人物時,您尋求的是什麼?您如何選擇他們?
DEO: 在面對這些採訪對象時,總有一種鏡像效應,尤其是在我寫人物特稿或傳記的時候。就我叔叔而言,寫他的故事,意味着講述一個教會我了解鄉村、了解土地的人的故事,也在某種程度上,讓我與墨西哥東北部達成了和解。我來自蒙特雷,這是墨西哥北部的一座城市,深受得州文化影響。我們就像狂野的得州人。那種文化總讓我的內心充滿矛盾,但在寫完我叔叔的故事後,我理解了許多伴我成長的文化特質。無論我如何否認,我的大部分作品都與蒙特雷有關。我拍了那部關於薩穆埃爾·諾約拉的紀錄片,他或許是蒙特雷最重要的詩人;我寫過一個叫阿萊霍·加爾薩·塔梅斯(Alejo Garza Tamez)的牧場主的故事,他在毒品戰爭中誓死保衛自己的財產;我寫的關於“澤塔斯”和“錫那羅亞”販毒集團的書中,也有好幾章與此相關。就像我總是重返1990年代一樣,我也總是重返墨西哥東北部。這就是我叔叔的故事帶給我的。
至於卡洛斯·斯利姆,我是在報道了2006年瓦哈卡人民大會反對州政府的起義之後,才開始着手為他寫傳記的。同年,我還目睹了聯邦、州和市的武裝力量在聖薩爾瓦多阿騰科鎮的殘酷鎮壓,警察在那裡強姦了許多女性。我還跟進了帕斯塔德孔喬斯的礦難危機(65名礦工遇難),以及在拉薩羅·卡德納斯、弗雷斯尼洛和卡納內阿等地的抗議活動。
2006年是劇變之年,這引發了我的思考:在我親眼所見、親身經歷、親筆記錄的這個國家,怎麼可能同時存在着世界首富?就在那時,2007年,斯利姆首次被《福布斯》雜誌評為世界首富。這種衝突深深地刺痛了我,我發現關於他的信息少之又少。這本傳記就始於這種思想上的交鋒。我總是試圖將不同的人物、思想和立場並列呈現。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意識到,拉丁美洲的新聞報道在描繪不公和不平等的社會時非常有力,卻很少能成功接觸到精英階層。這便是我開始報道斯利姆的起點。
GIJN:您曾說過,在採訪難以接觸的人物時,比如大毒梟“馬約”·桑巴達(Mayo Zambada),記者必須讓自己沉浸其中。您能談談這個過程嗎?
DEO:要實現這種沉浸,你必須先介紹自己,說明你是誰,以及你對這次會面有何期待。這是我在所有互動中都會做的事。當我接觸某人時,我會告訴他們:我來找你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我有這個困惑,我想理解這個問題。我會坦率地講出我對他們的疑問,並且努力保持尊重,即使面對的是我持強烈批判態度的人。我採訪過殺人犯,採訪過那些讓別人人間蒸發的人,他們讓我怒火中燒。即便如此,如果那個人願意分享一些對我來說有意義的經歷,那麼我就必須保持尊重——不是對他們陳述的事實版本保持尊重,而至少是在會面期間保持尊重。
在極端情況下,比如我與“馬約”·桑巴達的交談,這不僅是為了建立共識、實現我所尋求的沉浸感,更是出於安全考慮。在那次會面之前,我所有的溝通都是通過第三方進行的。那是一個黑手黨的世界,一個陰影中的世界,那裡的一切未必都像表面看到的那樣。所以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當桑巴達和我見面時,他能親耳聽到我是誰,而不是只聽信別人的轉述。我要告訴他,我不是為了錢而來,除了想要理解事實之外,我沒有任何別的企圖。在那個基礎上建立一種對話關係,不是將對方客體化,而是兩個主體之間的交談。一個主體想要理解某件事,而另一方可以幫助他做到這一點。
GIJN:您記述了過去幾十年來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悲劇,以及毒品戰爭的方方面面。每一段故事都伴隨着痛苦與複雜,您是如何賦予它們各自獨特的面貌的?
DEO:我努力踐行的新聞報道,是一種不僅調查,而且沉浸其中的報道。以ABC託兒所的火災為例。火災發生在6月5日,星期五。我第二天就趕到了。當時還不知道有多少孩子遇難,傳言是五個或十個。政府已經在試圖掩蓋真相,我意識到事情背後另有隱情。我記得到了周一,當官方確認死亡人數時(超過49名兒童死亡,上百人受傷),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湧來報道這場近乎聖經故事般的悲劇。我當時供職的報社讓我去參加孩子們的葬禮,拍攝並採訪家長。我斷然拒絕了:對於一場大火奪走一個孩子的生命所帶來的痛苦,我還能說些什麼來增加它的分量呢?
於是,我轉而開始調查一份文件,文件顯示一些政府官員的名字赫然出現在託兒所所有人的名單上。這是墨西哥社會保障局(IMSS)以一種非常隱蔽的方式,不負責任地將服務外包所導致的結果……我把焦點放在了這一點上,沒有去採訪任何一位父母。
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研究和記錄事件的來龍去脈,但始終是從腐敗的角度切入。在我看來,那才是火災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麼空調故障。七個月後,一位名叫羅伯托的父親在和我喝咖啡時對我說:“嘿,你為什麼從來沒問過我的故事?”我告訴他:“因為我在這裡是為了傾聽。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揭露腐敗,讓你們的訴求被看見。”“但我想告訴你我的故事,”他說。他之所以願意開口,正是因為我一直都在那裡。
當那種沉浸發生時,一定是因為你已經在那裡待了很久,你具備了傾聽的能力,並且有足夠的耐心。當今世界對任何事情都沒有耐心;人人都想要立竿見影,追求速成。但耐心才能實現沉浸。耐心或許無法讓你真正“理解”——我永遠無法理解因腐敗引發的大火而失去孩子的悲劇——但它能讓你在一個悲劇性的、歷史性的公共事件中,觸摸到人性的脈搏,感受到人性的存在。而我認為,在我的報道中傳遞這種人性,至關重要。
 Diego Courchay 是《德拉科特評論》(The Delacorte Review)的副主編,也是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撰稿人。他曾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旗下的TELEMUNDO電視台擔任新聞製片人,並為埃菲通訊社、《關係》(Nexos)雜誌和《過程》(Proceso)雜誌擔任記者。他畢業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能用英語、西班牙語和法語進行寫作和報道。
Diego Courchay 是《德拉科特評論》(The Delacorte Review)的副主編,也是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撰稿人。他曾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旗下的TELEMUNDO電視台擔任新聞製片人,並為埃菲通訊社、《關係》(Nexos)雜誌和《過程》(Proceso)雜誌擔任記者。他畢業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能用英語、西班牙語和法語進行寫作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