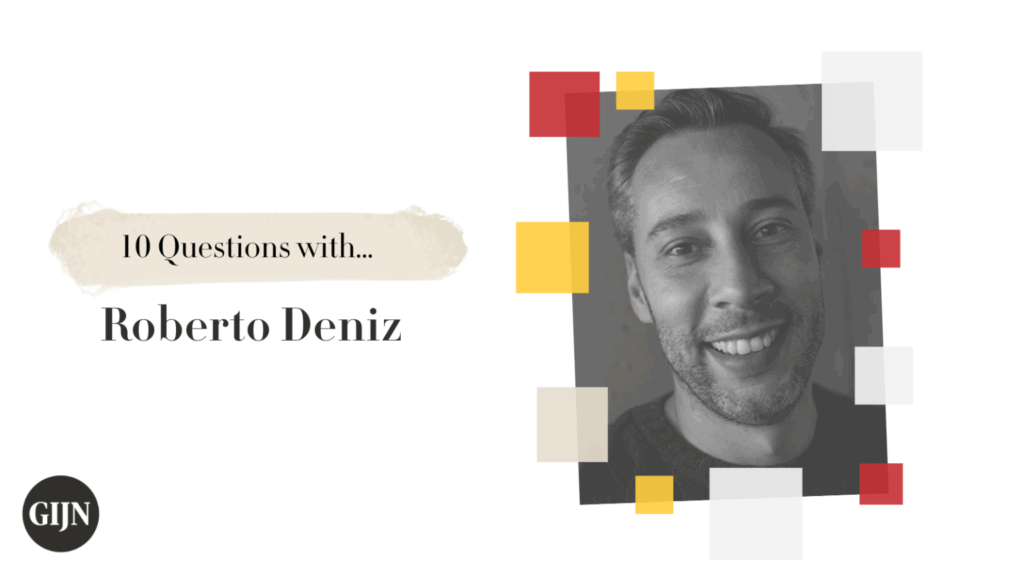近年來,環境調查報道日益受到關注。在污染、農藥和有毒物質等議題尚未被視為足夠“高大上”的調查素材時,法國《世界報》(Le Monde)的調查記者斯特凡妮·奧雷爾(Stéphane Horel)就已經開始關注這些議題。
作為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2024年的新成員,奧雷爾還致力於調查科學領域的虛假信息傳播和遊說集團的影響力。在超過20年的職業生涯中,這位認為從事調查報道是自己本能的記者獲得了眾多獎項,其中包括路易斯·韋斯歐洲新聞獎(Louise Weiss Prize for European Journalism),以及因主導“永久污染”(Forever Pollution)項目而獲得的2024年歐洲年度科學記者獎。此外,她還與斯特凡·福卡特(Stéphane Foucart)共同完成了“孟山都文件”調查,並因此獲得了2018年歐洲新聞調查獎。
雖然她的調查工作嚴謹科學,但這位曾是俄羅斯文學專業的學生在業餘時間喜歡製作拼貼畫——其中一些作品還被用作她的著作封面。她在調查中採用富有創意的方法,文筆細膩,還不忘適時添加一些幽默元素。
GIJN: 在你參與過的所有調查中,哪一個是你最喜歡的?為什麼?
斯特凡妮·奧雷爾: 我最喜歡的調查永遠是剛剛完成的那一個,因為我的心思還沉浸其中。在“永久污染”和“永久遊說”這兩個項目中,我花了三年時間研究 PFAS(永久性化學物質)造成的污染問題,這個過程讓我深深着迷。這是我首次涉足工業污染領域的調查,能夠讓這個此前如同污染本身一樣無形的議題浮出水面,着實令人振奮。我們在2023年2月發布的污染地圖揭示了 PFAS 在歐洲的污染程度,這迫使公眾認識到工業污染的嚴重性,以及當前監管缺失所導致的惡果。整個團隊為了公共利益而努力,成功將這個議題從環保部門的層面提升到政治和歐盟層面,這讓我們感到莫大的滿足。
這個項目的執行方式也令人振奮。對我來說,協調跨境調查是一次全新的嘗試。這就像圍繞一個特定主題組建一個小型運營編輯團隊:你需要讓一群大多互不相識、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記者達成共識並投入工作,而且你與他們之間並沒有任何層級關係。這既是專業上的挑戰,也是人際交往的考驗,但我真的很享受這個過程。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開創了多項新方法,尤其是如何在保持編輯獨立性的同時,有效整合專家和科學家的專業意見,確保信息準確性。這就是我們所倡導的”專家審核新聞學”模式。
GIJN: 對於您所在的國家/地區,調查性報道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斯特凡妮·奧雷爾:與在拉美或亞洲國家報道環境問題的記者相比,我覺得抱怨某些工作條件幾乎有些不當。在那些地方,記者面臨的風險不是應付公司的不愉快騷擾,而是可能一顆子彈就要了命。
以前被問到是否受到壓力時,我總是笑着說:“從來沒有,我只是在家裡穿着粉色拖鞋安靜地工作。”但在這次調查中——其中涉及數千億歐元的利益,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了安全問題。有人試圖闖入我家,我在咖啡館的包也被偷……這些也許只是巧合,但我還是報了警,報社也向檢察院報告了此事。這些並不妨礙我繼續工作,但確實讓人感到不安。
就法國的調查性新聞而言,存在着價值認同的問題。我們是歐洲少數幾個沒有調查記者協會的國家之一,這種集體性和專業性反思的缺失是一個重大缺陷。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具有濃厚文學色彩的報道文學更受重視。事實上,法國最負盛名的新聞獎項阿爾貝·倫敦獎(Prix Albert Londres)就是授予這類新聞作品。在法國,人們也傾向於把調查性新聞等同於政治財經報道。因此,要說服編輯部重視其他調查主題並不容易……比如需要長期跟蹤才能揭露工業污染等系統性問題的調查報道就很難獲得支持。
GIJN: 作為調查記者,您遇到的最大障礙或挑戰是什麼?
斯特凡妮·奧雷爾: 直到最近,我研究的主題(農藥、化學品接觸)都不被視為調查報道的題材。2008年,當我寫第一本書《大入侵》(The Great Invasion)時,這本書調查了那些污染我們日常生活的產品,但在科學圈子之外,這個話題幾乎沒人關注。因為這被認為是一個“消費者”話題,而且因為我是女性,我的出版商最初想做一個非常少女風格的封面。儘管我基於所有相關科學文獻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但它仍被當作“女性話題”來對待。
我做了很長時間的獨立記者。作為一名專註於這些被錯誤地認為不適合調查報道領域的調查記者,要開拓自己的道路並建立公信力並不容易。
GIJN: 您有什麼採訪技巧可以分享?
斯特凡妮·奧雷爾: 採訪是一次交流。如果你對受訪者不感興趣,就別期待他們會說出有趣的內容。即使面對的是為農藥辯護的說客,我也會試圖了解對方是什麼樣的人。我總是努力發現職業背後的人性。
在採訪頂尖科學家時,千萬不要一無所知就去問一些基礎問題。這是對他們專業知識和寶貴時間的不尊重。在採訪專家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課”。這種前期準備工作不僅是一種尊重,也能讓你和他們進行真正深入的對話。
GIJN: 在調查工作中,你最喜歡使用的報道工具、數據庫或應用是什麼?
斯特凡妮·奧雷爾: 我想到的其實是一個編輯方法:幽默。用幽默的方式來處理某些議題,能夠揭示出一些原本看不到的含義。
比如在 PFAS 調查中,我們整理了一份產業遊說團體最具代表性的威脅言論,取名為“末日就在眼前”。其中有典型的經濟要挾(“我們將不得不裁掉這麼多人”),但有時候企業家的說法荒謬到令人發笑,比如一個歐洲製藥行業遊說組織聲稱,禁止 PFAS 將導致歐洲所有製藥生產停擺。
幽默不僅能讓報道更有趣味性,還能幫助我們抵禦議題本身的沉重。畢竟,將有數十萬人會因此患病死亡。如果沒有幽默幫助我們保持一定距離,這種話題足以讓人陷入抑鬱。
GIJN: 在你的職業生涯中,收到過的最好建議是什麼?你對有志成為調查記者的人有什麼建議?
斯特凡妮·奧雷爾: 對我來說,最關鍵的是信任。我永遠不會忘記在職業生涯中信任過我的人,因為信任就是賦能。正是因為這種信任,我才能在調查記者這條路上找到方向。
現在,當我有機會與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記者合作開展調查時,我也試圖回報這種信任。看到被給予空間的記者,包括一些從未真正做過調查報道的人,最終成為項目的中堅力量,帶來新的視角,這種轉變有時會讓人感到神奇。
GIJN: 你最敬佩的記者是誰?為什麼?
斯特凡妮·奧雷爾: 我非常敬佩我在《世界報》的同事斯特凡·福卡特。我們曾一起調查孟山都文件,並在2020年合著了一本關於科學虛假信息的調查報道《理性的守護者》(The Guardians of Reason)。這不僅是智識上和友誼上的相遇,也是一份感激,因為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他,我才能加入《世界報》。他的思維敏捷度以及不斷提升高水平科學素養的能力,總是讓我印象深刻。
GIJN: 你犯過最大的錯誤是什麼?從中學到了什麼?
斯特凡妮·奧雷爾: 我在實踐中明白,協調跨境項目並不總是與民主劃等號。有時候,你不得不做出一些團隊部分成員不喜歡的決定,這會產生一些需要學會處理的矛盾。為了集體利益做決定,並不意味着你就是獨裁者。
在上一個項目中,我創建了一個45人的集體任務,目的是收集行業遊說論據,但結果並不理想,因為有些同事不理解這種方法。這很正常,畢竟每個人的思維方式都不一樣。說到底,這還是關於信任:讓人們發揮自己的技能和才能。
GIJN: 你如何避免職業倦怠?
斯特凡妮·奧雷爾: 職業倦怠在我們這個行業乃至整個社會都是一個普遍問題。我曾經因為工作和個人壓力的雙重夾擊而住進重症監護室。當時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實在承受不了。雖然我熱愛我的工作,到現在依然工作過度,但我已經學會警惕。我在冰箱上貼了一條提醒:“你和你的工作同樣重要。”
我的一個自我保護措施是,在項目結束前的每個階段,我都會確保每周留出一天完全不工作。統籌調查報道會帶來很大的心理負擔,在那一天里我要麼和朋友相聚,要麼就癱在沙發上看書,總之不做任何決定。
GIJN: 你覺得調查新聞工作中最令人沮喪的是什麼?你希望未來能有什麼改變?
斯特凡妮·奧雷爾: 跨境新聞合作和集體智慧很令人興奮,但我覺得現在項目有過度擴張的趨勢。這導致調查深度不夠,卻要付出過度的精力。我特別擔心自由職業記者的狀況,他們往往同時要進行三四項調查。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新聞編輯部,要想專註於一個調查項目幾個月仍然很困難。
 Alcyone Wemaëre 一位常駐里昂的法國自由職業記者,曾在巴黎的Europe1和France24擔任記者。除了擔任GIJN的法語編輯,她還是里昂政治學院的副教授,共同負責新聞專業“數據與調查”方向的碩士課程。
Alcyone Wemaëre 一位常駐里昂的法國自由職業記者,曾在巴黎的Europe1和France24擔任記者。除了擔任GIJN的法語編輯,她還是里昂政治學院的副教授,共同負責新聞專業“數據與調查”方向的碩士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