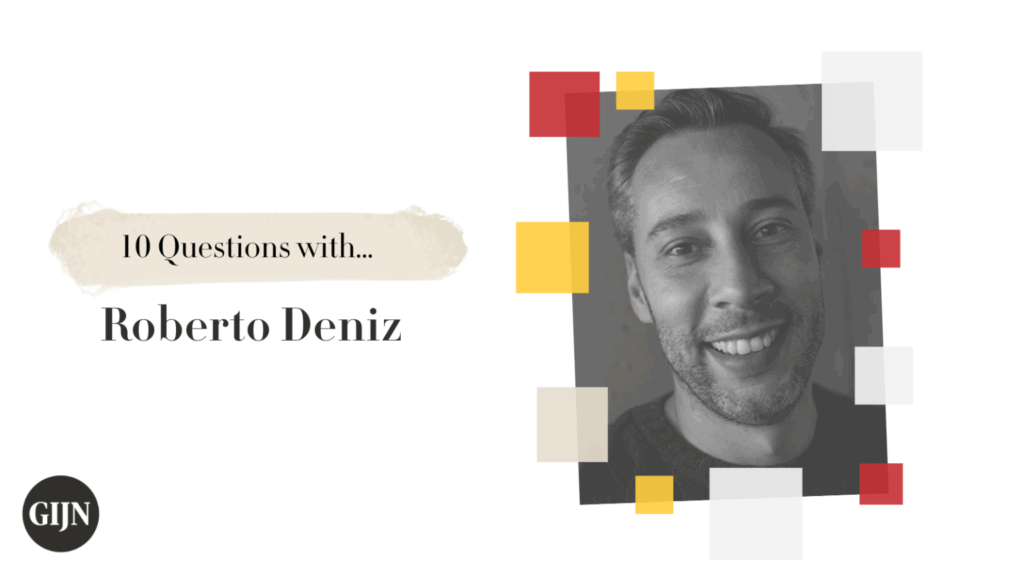插畫:Smaranda Tolosano for GIJN
翻閱凱特·麥克萊蒙特(Kate McClymont)在《悉尼先驅晨報》的報道檔案,如同窺探澳大利亞的陰暗面:從政治腐敗到有組織犯罪,從房地產醜聞到權貴醜事,她的報道常常觸及那些位高權重者,或是那些不擇手段、通過踩踏他人而暴富的人物。
作為《悉尼先驅晨報》的首席調查記者,麥克萊蒙特曾多次獲獎。她最近製作的一檔播客深入報道了一位悉尼女商人策劃的龐氏騙局,這起案件最終演變成總額高達2300萬澳元(約1500萬美元)的特大詐騙案。

調查播客《謊話連篇》深入追查澳大利亞史上最大龐氏騙局的主謀,由凱特·麥克萊蒙特擔任聯合主持人。圖:蘋果
這檔名為《謊話連篇》(Liar Liar)的播客深入挖掘了梅麗莎·卡迪克(Melissa Caddick)的故事:一個普通學生如何搖身一變成為自封的理財專家,誘騙親友將畢生積蓄和養老金交給她投資。這些錢很快被她揮霍在奢華旅行、房產投資上,或用於滿足她對名貴珠寶和奢侈品服裝的痴迷。
在警方突擊搜查其住所後,卡迪克隨即失蹤。後來她的一隻腳在澳大利亞海灘上被衝上岸,驗屍官最終宣布她已死亡。用麥克萊蒙特的話說,她是一個“反社會的騙子”,製造了澳大利亞本世紀最大的詐騙案。這檔節目大受歡迎,也為麥克萊蒙特贏得了自己第九個沃克利獎——澳大利亞新聞界的最高榮譽。
在播客中,聯合主持人湯姆·斯坦福特(Tom Steinfort)對麥克萊蒙特在悉尼有組織犯罪領域的淵博知識讚嘆不已。每當他們談到某個地方的舊案時,他總會感慨:“凱特·麥克萊蒙特,你簡直就是一部百科全書!”
因為報道工作,她曾多次收到死亡威脅,面臨諸多法律挑戰,甚至在孩子尚小時不得不暫時躲避——不是因為報道黑手黨,而是因為調查某支球隊後需要躲避憤怒的足球球迷。
她1985年開始在《悉尼先驅晨報》工作,1990年左右轉去做調查報道,2025年就迎來從事新聞業的40周年。她最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她並沒有放慢腳步的打算。“當人們問‘你要退休了嗎?’我就說‘不會,我會死在打字機前’,”她說,“我覺得沒有比這更好的謝幕方式了。”
GIJN: 在你參與過的所有調查中,最喜歡哪一個?為什麼?
凱特·麥克萊蒙特: 這很難回答。調查梅麗莎·卡迪克案件在某些方面非常精彩,因為在調查過程中你並不知道結局是什麼。隨着調查推進,案情逐漸展開,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我完全是偶然發現這個故事的。當時我在調查一個商人的搜查令,就打電話給負責執行搜查的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問:“能告訴我你們在沃拉羅伊路執行的搜查令情況嗎?”他們回答:“讓我看看…等等,你說的是沃拉羅伊路還是沃蘭加拉路?”因為這兩處搜查是同一天進行的。他們說那是針對一個叫梅麗莎·卡迪克的人。我最初以為她與那個商人有關聯,於是查了公司登記,接着就發現她已經失蹤了。
我不能說這是我最喜歡的調查,但我多年來一直追蹤一個叫埃迪·奧貝德(Eddie Obeid)的腐敗政客的故事——確實是很多年,我從1999年就開始寫他。他起訴我誹謗,而且勝訴了。當時我覺得再也不能寫這個人了。但我堅持下來,當他最終入獄時——現在他因為我報道的事已經兩次入獄——我忍不住哭了。這個過程太艱難了,他還經常在議會裡詆毀我,所以這可能是我最有成就感的調查。我不能說這是最有趣的,因為除了被起訴外,他還雇私家偵探跟蹤我。這並不好玩,但能夠為公眾利益服務,揭露腐敗並讓他們付出代價,這種滿足感是無與倫比的。
GIJN: 在你們國家,調查報道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凱特·麥克萊蒙特: 實際上是我們的法律制度。悉尼被稱為世界誹謗訴訟之都,人們動不動就提起訴訟。我曾被一位96歲老人起訴,他聲稱我報道他40年前的案件導致他經濟損失。雖然他在案件開庭前就去世了,但我每寫一篇報道都必須考慮可能面臨的誹謗風險。你必須自問:如何在法庭上證實這個報道?某種程度上我們就像警察,要考慮是否有信源願意在法庭上作證。這些顧慮總是伴隨寫作過程,確實不利於報道工作。我認為澳大利亞很多媒體因此放棄某些報道,對國內新聞產生了寒蟬效應。那些富有、知名且好訟的人財力雄厚,許多機構不敢冒險,因為他們肯定會發起訴訟。
我已經被起訴約五次……而且常在發稿前收到威脅。你只能咬緊牙關挺過去——但比死亡威脅更可怕的是訴訟,這意味着數月的庭審和巨大壓力,真的要盡量避免。
我收到過幾次死亡威脅。不過我銘記一位警察朋友的話:“凱特,真正要擔心的是那些不發出威脅的人。”有次威脅信直接送到我家,那是在我報道一個人在9歲孩子面前被槍殺後的一周。這確實有點可怕,但你必須把它視為恐嚇,不能因此停止工作。如果被嚇住,就無法做新聞。而且我覺得,殺害記者對他們來說也不明智。
在澳大利亞做新聞,考慮到我們的社會環境,我們還是比較樂觀的。如果是在俄羅斯或南美等地區報道,我肯定沒有這麼大勇氣。我認為那些地方的記者才是真正的勇士。
GIJN: 在從事調查記者工作期間,你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凱特·麥克萊蒙特: 埃迪·奧貝德那個案子是最大挑戰。在被他成功起訴後,我曾停筆半年,擔心繼續報道會被視為發泄怨氣或報復行為。所幸最終證據確鑿,真相大白。但知道有人專門雇調查員挖掘你的把柄用來要挾,這種感覺確實很不舒服。
GIJN: 你有什麼採訪技巧可以分享?
凱特·麥克萊蒙特: 學會做個業餘心理學家。了解受訪者的性格特點,選擇最適合的溝通方式。我通常這樣開場:“希望您能幫助我……”,盡量讓對方放鬆、不感到受威脅。始終保持禮貌,即使對方辱罵或發火,也要冷靜回應:“我很抱歉您有這樣的感受,我們能談談嗎?”
禮貌常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當然,有時可能需要採取更強硬的態度。關鍵是讓對方繼續對話,對話時間越長,獲得的信息就越多。最理想的是面對面交談。我明白新聞工作時間緊迫,但爭取面對面交流通常是值得的。
GIJN: 你在調查報道中最常用的工具、數據庫或應用是什麼?
凱特·麥克萊蒙特: 我使用的是一個相當昂貴的工具。這是《悉尼先驅晨報》使用的一個程序,可以搜索澳大利亞證券投資委員會的數據,用於查詢公司信息、房產信息等。我幾乎每天都會用到它。我甚至不敢計算自己給公司花了多少錢,因為每次搜索需要30澳元。在調查某人時,我首先想了解的是他們擁有哪些公司、與誰有商業往來、公司是否註銷、是否欠稅等。這個系統還能顯示他們的出生日期、住址和過往的商業夥伴,這些信息能幫我逐步描繪出調查對象的全貌。
但每次搜索需要30澳元,費用會迅速累積,這也是為什麼只有較大的媒體機構才能負擔得起。
GIJN: 到目前為止,你職業生涯中收到的最好建議是什麼?你對有志成為調查記者的人有什麼建議?
凱特·麥克萊蒙特: 我認為最好的建議就是要學會合作。雖然有時我們是競爭對手,但歸根結底我們都為同一個目標而工作。如果其他機構的記者向我求助,只要不涉及我正在調查的內容,我都很樂意提供幫助。要明白你可以向他人求助,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永遠不要害怕提問。
由於媒體行業的壓縮,我在時間上有一定優勢,可以花幾周時間認真完成一個報道。但對於每天應付繁重工作的年輕記者來說就很困難了。所以我經常建議他們,如果發現好的選題,可以找資深記者說:“能和我一起做這個報道嗎?”這種合作對雙方都有益處,因為我能傳授經驗,而年輕記者在其他方面也很優秀,這是一種很好的工作模式。
GIJN: 你最敬佩的記者是誰?為什麼?
凱特·麥克萊蒙特: 我最敬佩的是美國記者帕特里克·拉登·基夫(Patrick Radden Keefe)。我剛讀完他的《疼痛帝國》(Empire of Pain),這本書講述薩克勒家族(編註:一個美國經商家族,曾擁有普渡製藥以及後來創立的萌蒂公司)的故事。目前我正在閱讀他的另一部作品《保持沉默》(Say Nothing),主題是愛爾蘭動亂時期的故事。他不僅具有出色的調查能力,還擁有極佳的文筆,這種雙重天賦着實令人欽佩。
GIJN: 你犯過最大的錯誤是什麼?從中學到了什麼?
凱特·麥克萊蒙特: 我最大的失誤是將兩個同名人物混淆了。由於這個錯誤,整本書不得不銷毀重印,重新發行正確版本。
另一個錯誤出現在一起謀殺案報道中。案件涉及一名男子涉嫌將女友推下致死,我在寫作時把“米/秒”誤寫成“千米/秒”。一位讀者來信指出:“按照你的計算,受害者都能飛到月球上了。”這完全是我的疏忽。人難免會犯錯,關鍵是要勇於承認。發現錯誤後應立即向相關方報告,不要試圖掩蓋。要以誠相待,道歉並積極補救。
GIJN: 你如何避免職業倦怠?
凱特·麥克萊蒙特: 我今晚剛和人談起,目前我在同時與不同記者合作五個報道,感覺每個都未盡如人意。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我也在摸索解決之道。對於如何避免倦怠,我的建議是需要休息時就該休息……好好睡一覺,第二天重新出發。
有時確實會感到疲憊和煩躁,但就像今天,我在與同事合作一個報道時,從法院文件中發現調查對象竟是一個在意大利被通緝的黑手黨成員。只要有新突破,工作疲憊感就會瞬間消失,重新燃起幹勁。往往只需幾個關鍵發現,就能讓人重獲活力,這種感覺確實奇妙。
GIJN: 對於調查新聞的工作,您覺得有什麼令人沮喪的地方,或者希望將來會有什麼改變?
凱特·麥克萊蒙特: 我最大的期望是能更便捷地獲取法院文件和證據。我非常羨慕美國記者享有的便利條件,那裡的法律體系對新聞工作者十分友好。相比之下,在這裡獲取案件記錄或法院判決等資料始終充滿困難和挑戰。
新聞工作最美妙的地方在於每一天都不盡相同。回首往事,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能夠從事一份如此熱愛的工作——雖然不是每時每刻都那麼完美——但這絕對是世界上最精彩的職業。
2023年,麥克萊蒙特憑藉其傑出的新聞貢獻,在澳大利亞第68屆沃克利獎頒獎典禮上獲得表彰(獲獎感言見以下視頻)
 Laura Dixon 是 GIJN 高級編輯。她曾在哥倫比亞、美國和墨西哥從事新聞報道工作,其作品先後見諸《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和《大西洋月刊》等知名媒體。她曾擔任倫敦《泰晤士報》特約記者,並獲得國際女性媒體基金會、普利策中心和”記者促進透明”組織等機構的資助與獎學金支持。
Laura Dixon 是 GIJN 高級編輯。她曾在哥倫比亞、美國和墨西哥從事新聞報道工作,其作品先後見諸《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和《大西洋月刊》等知名媒體。她曾擔任倫敦《泰晤士報》特約記者,並獲得國際女性媒體基金會、普利策中心和”記者促進透明”組織等機構的資助與獎學金支持。